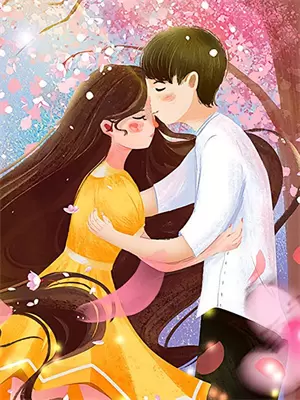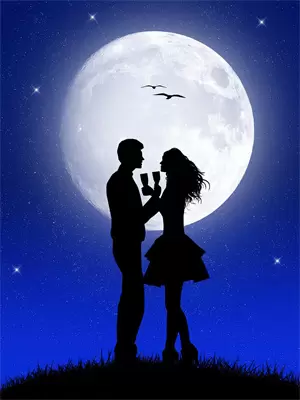财叔五十来岁,是镇上医院的守夜人。白天除了忙自家的农活,得空也常去熟人家里帮闲,
他与我家沾点亲,因此常被请来帮忙。以前财叔来我家干活,到了晚上闲下来时,
我总爱缠着他,拽着他的胳膊,非要他讲几个鬼故事才肯罢休。夏日的傍晚总算来临。
忙活一整天的大人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地聚在街边乘凉,拿着蒲扇摇着风。
我瞅见财叔收了工、吃完饭,正眯着眼躺在竹椅上歇息,趁着他还没回医院,
便赶紧泡了杯茶递过去。我顺势蹲在竹椅旁,胳膊肘撑在椅边,压得竹椅“咯吱”轻响。
"财叔,给讲个故事呗"财叔看了看我,抬起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
"给你讲能成。"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听了夜里睡不着,可不要怪我。
"一、红褂子{伤心的人,最好哄}老家的土坯院墙内,藏着太多阴恻恻传说。
昔时院墙内的的农村婆娘常常深陷于命运的泥沼,稍有不顺,便极易走上绝路。
被男人的拳头砸在脊梁上。被婆婆的尖酸话剜着心。
或是跟左邻右舍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吵红了脸。心里那点气就像盖在地里晒的麦秸,
闷在胸腔里,一丁点儿火星就能烧起来。这火烧起来便收不住了。房梁上的绳子。
窗台上的农药。院子里那口,深不见底的井。都成了去处。往往是前一刻还在灶台边抹眼泪,
后一刻就寻了短见,快得让人来不及拽一把。村里人说起这个,总压低了声音。
说不是她们自己要走,是有东西在旁边缠着呢。那东西能化成人形,
专往心里有窟窿的人身上凑。你越气,它越欢,
像只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作响....."死了就好呀。""一了百了,
比在这世上受煎熬强。"那声音黏在人的耳旁,带着秽气,不理它,它就天天说,夜夜说,
说得你眼里的光一点点灭了。最后真觉得那条路是唯一的出路。也有另一种嘀咕,
不是鬼找上来,是自个儿心里的怨结出了窍。气憋得久了,就成了勾魂的引子,
把那些游荡的东西招来了。它们本是些投不了胎的孤魂,闻着这股子怨气,就赖着不走了,
成了附骨的蛆。屋里饭桌垂下来一根绳子、窗台下歪倒着药瓶、井轱辘还在滴溜溜的转。
人没了,那声音也跟着散了,只留下屋檐下的蛛网,
在风里晃啊晃......老王家的媳妇桂枝,近来心情糟糕透顶。丈夫整日在外打牌,
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婆婆也没个好脸色,横竖都能挑出刺来。下午繁重的农活干完,
桂枝坐在院子里,眼神空洞,脑袋里乱糟糟的。忽然,一个穿着红褂子的女人,
悄无声息地从门外飘然而至,站在了桂枝身旁。那女人嘴唇开合,嘈嘈切切地说着什么,
声音像从极远的地方传来。又仿佛直接从旁边钻进了桂枝的脑子里。仔细听,
那声音一会儿像是在轻声同情桂枝的遭遇,一会儿又像是在急切地劝说她去做什么事。
桂枝只觉脑袋愈发懵了。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
她的目光渐渐被那红褂子女人吸引。仿佛陷入了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
"你看这日头落得多快。""男人不顶用,婆婆磋磨人,
这日子熬到啥时候是个头哟……"她不停的在桂枝左右絮叨着。
身上的红褂子颜色暗沉得好似一片陈年的血痂。散发着一股陈旧而腐败的味道。
桂枝的两只手不停地抠着指甲,指甲缝里还嵌着晌午锄地时沾的泥。
“我男人拿走了买稻种的钱,我要拦着他,婆婆还骂我”桂枝的声音带着哭腔,
满心的委屈如决堤的洪水,再也抑制不住。
早上婆婆站在门槛上骂她是丧门星的场景历历在目。红褂子女人张着嘴笑出了声。“我知道,
我都知道的。”她的身体贴着桂枝,凉冰冰的。“瞧,这院子里井台磨的真光溜。
”“你闭着眼踩上去,脚一滑就什么都不用愁了。”红褂子压低着声音,
话语里带着蛊惑的意味。桂枝的视线慢慢移向院子里那口老井。井旁边的木桶盛着水,
斜阳在水面上晃出细碎的金光。反射出来照在桂枝的脸上,红褂子旋即又转到桂枝的另一边。
“去年你三婶家的姑娘。”女人继续压低着声音。“就是在井边寻的清净,
听说走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呢。”桂枝的喉咙突然发紧,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她看见红褂子女人脸很白像是糊了厚厚的一层粉。女人抬手理了理鬓角,
桂枝才发现她的指甲缝里也有泥,和自己的一模一样。“天快黑透了。
”女人往井的方向挪了几步,红褂子在暮色里晃成一团。“再晚些,
你男人赌钱回来又要打你了。”女人在井边招呼着。桂枝站起身来,
坐久的膝盖发出 “咔咔”的弹响。她的脚像踩着棉花,一步一步朝井台挪过去。
红褂子女人始终站在井边挥着手。桂枝和女人站在了一起,一只脚踩在了井沿上。
井里的水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水面晃荡着,影子就跟着颤。
一些画面不受控制地在她脑海里浮现,三婶家姑娘的笑脸和这口幽深的井重叠在一起。
“你还在等什么呢?这样的日子,早解脱早好。”红褂子女人的声音又幽幽响起。
桂枝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衣角,她的呼吸变得急促,望着那井口,心中涌起一股绝望的冲动。
她想起这些年所受的苦。男人的打骂、旁人的指指点点。生活就像一个无边的黑洞,
将她的希望一点点吞噬。此时,井里的水似乎在发出召唤。那是一个可以逃离痛苦的地方。
桂枝的脚步又往前踩了踩,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水面。那模糊的影子仿佛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在向她招手。就在她的脚快要完全站到井沿时。“哐当”一声清脆的响声传了过来。
是门口有一把刀掉在了地上。红褂子听见这声音,竟然立马抛开桂枝往后院跑去。
这时门外趴着一个人影,赶紧站起身来捡起了那把杀猪刀,往院内撵了过来。
等到了桂枝旁边,那人一把攥住她的胳膊往回猛拽。“哎哟”桂枝叫了一声摔在地上,
懵懵懂懂抬头时,才看清是村里那个常年围着油布围裙的王屠夫。
原来桂枝的丈夫今日在牌场赢了钱,恰好撞见收摊的王屠夫挑着担子路过。
便掏钱选了条五花肉,托他顺路送回家来,好让她晚上做道硬菜给自己解解馋。
那王屠夫刚到桂枝家门口,就望着院子里一个红衣服女人在桂枝旁边晃悠,
瞧着不像是本村的人,不知道在说什么,但里外都透着股邪劲。
前阵子村里王婶家的女儿刚遭了难,近来关于邪祟的传言正盛。他心里不免犯嘀咕,
怕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桂枝。王屠夫身强体壮,性子又凶,
但对着这未知的事物还是有些发毛。他壮了壮胆子,从挑子里拿了把杀猪刀踱着步子往里进。
这杀猪刀日积月累宰得猪没有千头也有百头了,按着农村的说话这刀早浸满了煞气,
亮出来邪祟见了都要退避三舍。王屠夫仗着这点底气往院里走,可心里终究有些发紧,
脚上被翘起的一块砖绊着了。只见一个踉跄,手中的杀猪刀竟脱手飞了出去。
杀猪刀重重地砸落在地,发出的这声响,在红褂子女人这听起来却不亚于一道惊雷。
“红褂子” 身形一闪,吓的跑了,转眼就没了踪影。桂枝的事很快全村子人都知道了。
村里一些胆大的后生结伴拿着杀猪刀、木匠尺、之类的物件,
在她家屋里屋外敲敲打打的转了几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过了没几天桂枝的娘家终于来了人将她接回了娘家去。她的丈夫和婆婆后怕不已,
慌里慌张请了阴阳先生来作法。折腾一场,也不过是求个心安。
这场风波就像夏日里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再有人提起桂枝家的事,
乡邻们也不过摇摇头,叹一声许是撞了啥不干净的,便再无人接话。
只是那些路过桂枝家门口的人,总忍不住加快脚步。
仿佛门缝后真有个穿红褂子的身影正往外窥视财叔从竹椅上猛地直起身子。
端着茶杯往嘴里吸溜了一口水,脸上的褶子夹杂促狭的笑意。
我慌忙合上因为被吓到而张开的嘴巴,指节无意识地攥紧了竹椅扶手。过了一会儿,
我拍了拍财叔的胳膊,声音里裹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财叔,再讲一个呗,我不怕的。
”财叔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行嘞,等我想一下,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顿了顿,他的眼神变得幽深,望向外面那片黑黢黢的街道。
“你知道老家传说里最凶的地方是哪里么?”我使劲摇了摇头,后颈的汗毛却倏地竖了起来。
“最凶的地方,就是戏班子放道具的二层小楼。”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带着点秘而不宣的诡异,“那是走霉运时,顺着木梯往上迈一步,都必要撞见吊死鬼的地方。
”“吊死鬼啊……”财叔拖长了调子,舌尖舔过嘴唇。“披散着头发遮着脸,
青灰色的长衣拖到地上,舌头伸得老长,垂在胸口晃悠。“那股子怨气哦,
能把月光都染成青的,凶得很,非常凶险的……”这几句话在脑海里形成的画面。
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牙齿都开始打颤,下意识地往财叔身边缩了缩,
胳膊肘紧紧抵住他的胳膊。二、戏班{锣鼓歇了,卸妆镜前只剩一层薄粉,
一吹就散}那还是几十年前的光景,老家还只是个小村庄。别说电视、电影,
连根电线都寻不着。日子清苦,最大的乐子就是逢集时跑去大集上,
挤在人堆里看戏班子唱戏,回来能高兴得好几天梦里都在翻跟斗。
偶尔也有小戏班顺着土路来村里。他们人少,得在村里找户人家借宿,
就在人家门口搭台唱戏,末了分些酬劳给主人家便是。戏谁都爱看,
可没人愿意留他们过夜——老辈人传下的话说,戏班子招阴,尤其是那些唱戏的行头,
放在家里不吉利。所以这类戏班通常只能找间废屋,或者去哪个胆大的老鳏夫家凑合着住下。
“记得那也是一个夏天。”虽然是傍晚,但日头还是把稻场的石滚子晒得发烫。
老头子们坐在门口吧嗒着烟袋,此起彼伏的知了声里,忽然听见有人在村口扯着嗓子喊。
“唱戏的来咯!”惊飞了一群麻雀。村里人纷纷站到门口张望,看来的到底是什么戏班。
我刚吃完晚饭,正趁着天光在家帮忙编筐,一听戏班来了,立马扔下筐子跑出去。
只见几个男人从村口的竹林边冒出来,扁担在肩头咯吱作响。两头挑着大红漆的木箱,
上面还用麻绳拴着锣鼓镲钹之类的家伙,一路走一路叮铃哐啷地响。后面又转出一个胖大汉,
穿着的确良蓝衬衫和灰裤子,脚踏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手里端着个大茶缸。他笑眯眯的,
一看就是班主。他身旁紧跟着一个妇人,时不时拿手帕擦额角的汗。她穿着白碎花红褂子,
配黑长裤,脚上是黑布鞋。料子虽是寻常土布,却做得十分合身,透着一股利落素净的气质。
后面又慢悠悠跟着几个老妈子,抱着包袱行李之类的东西。
一群胆大的毛头孩子围着戏班的行李打转,手痒地戳戳这个、摸摸那个。戏班越走越近,
我的目光又落回那个穿红褂子的妇人身上。待看清她的脸时,
整个人都怔住了——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往日里听戏、听说书,总提丹凤眼,
我原以为不过是眼型狭长些罢了,今日一见这妇人的眼,
才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丹凤眼啊!她眼角微微向上挑,眼下脸颊透着一抹天然的粉红,
一股勾魂摄魄的狐媚劲儿扑面而来。眼波流转之间,情意竟像化成了一条条绸带,
缠绕每一个望向她的人,叫人不由自主陷进去。我就那样呆呆地望着她。那妇人察觉了,
竟径直朝我走过来。我也因此更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即便到现在,
我也敢肯定:她生得那样美,而且绝对没有涂一点脂粉。“小伙子,你认识我?
”“今天日头好晒啊,我们要在你村唱戏哩。”这年我刚刚十三岁,
头一回被人叫做“小伙子”,而且还是被这么一个漂亮得晃眼的女人叫。
一股热气“嗡”地冲上头顶。我猛地抬起头,又慌得赶紧低下,心里像揣了面鼓,
咚咚咚敲得震天响——她怎么会跟我说话呢?等我终于攒足勇气想要回答时,
她已经随着人群走进了村里。戏班子最后落脚在村里养鸭子的老王头家。
选这儿理由再简单不过——他家门口那片空地格外宽敞,正好能搭台唱戏。唯一麻烦的是,
老头一个人住,屋里屋外都邋遢得下不去脚。好在戏班里的妇人们个个手脚麻利,
才放下行囊,就主动洒扫收拾起来,互相欢快的吆喝声顷刻间驱散了屋里的沉寂。
仿佛转眼间就要把那破败小屋变了模样。男人们则另有分工,搭戏台是头等大事。
不过乡下唱戏对台子要求本就不高,加上班主会来事,赔着笑脸,忙着散烟,
几句话就招呼来不少看热闹的村民帮手,
不一会儿木槌敲打桩子的咚咚声、村民们粗声大气的号子声就响成一片。搭建过程简单高效,
他们先在空地上划出区域,四角立起粗实的木柱,顶上再蒙一层防雨的油毡布,
一个简易戏台的框架便出来了。为添些正式的气氛,他们在台口两侧的柱子上架起一根木梁,
梁上还缠着几缕褪了色的红绸,风一吹,那绸子便软塌塌地飘动起来,虽不鲜亮,
却也透着几分唱戏的热闹劲儿。夜幕将垂未垂之际,村里的大戏终于开锣。
大人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纷纷扛起长条凳、拎着竹椅马扎,从四面八方涌来,
团团围在戏台前。待天色彻底沉暗,戏班里走出两个人,蹲在台边开始侍弄一盏汽灯。
“呼哧、呼哧”一个人在给汽灯打着气。随即另外一人划亮了一根火柴,凑近里面的灯芯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