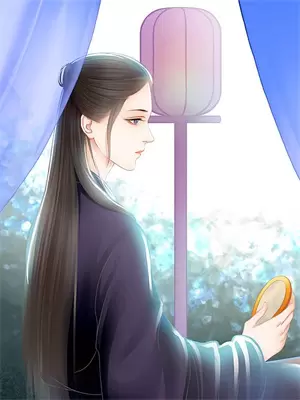无影灯的光线像一场冰冷的暴雪,覆盖了解剖室里的一切。福尔马林与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像冰针般提醒我一个事实——我,顾言,已经死了。
我像一缕无形的烟飘浮在半空,注视着解剖台上的自己。尸体皮肤因失血而呈现蜡质的灰败,脸上那抹诡异的上扬微笑,却赋予了这张死亡面具一丝邪气的生动。
林若雪就站在这具“我”的旁边。
她穿着蓝色解剖服,戴着口罩和手套,只露出一双清冷的眼睛。那曾是我最熟悉的眼神,冷静、专注。她是市局最出色的主检法医,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唯一想过共度余生的女人。此刻,她的眼神里却多了一丝疲惫与困惑。
“死者,顾言,男,27岁。初步判断死亡时间超过72小时。”她的声音平稳而专业,像在朗读一份无关的报告。“体表无明显外伤,面部肌肉呈痉挛性收缩,形成‘微笑状’,符合窒息死亡的典型特征……”
我的目光落在她握刀的手上。在她右手手套的腕口边缘,一丝极淡的新鲜红色划痕若隐若现。我的意识核心猛地一沉。
刀锋落下。我感觉不到疼痛,却能清晰地“回忆”起刀刃划破皮肉的触感,一种灵魂与肉体被剥离后残留的冰冷共振。
她熟练地打开我的胸腔。那颗曾为她剧烈跳动过的心脏,本应安静地躺在里面。
但那里,空空如也。
林若雪的动作停滞了。她俯下身,用镊子在胸腔内仔细探查,随后缓缓直起身,摘下口罩。那张素净的脸上,血色尽褪。
“心脏不见了。”她的声音轻如气音,却在我虚无的意识里激起巨浪。
怎么会?
“不可能……”一个沙哑的声音从我喉间挤出。
林若雪猛地回头,锐利的目光扫向我所在的方向。“谁在那里?”她的声音透着警惕,右手握紧了手术刀。
我这才意识到,她听得到,但看不见我。我闭上了嘴,巨大的悲伤与荒谬感攫住了我。我成了自己谋杀案的唯一“目击者”,一个无法作证的亡魂。
解剖室的门被推开,实习生小刘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林医生!张队那边有新发现!”
林若雪重新戴上口罩,掩盖瞬间的失态。“说。”
小刘举起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几片微小的碎屑。“我们在死者……顾言的指甲缝里,发现了残留的皮屑组织。”
那是我在生命最后一刻,拼尽全力留下的线索。我记得那双扼住我喉咙的手,记得指甲深深嵌入凶手皮肤的触感。
“DNA比对结果出来了?”林若雪问道,开始用生理盐水冲洗我的胸腔。
“出来了。”小刘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惊恐,“所以张队才让我立刻过来……”他停顿了一下,“是……是你的。”
“哐当——”
林若雪手中的不锈钢镊子掉落在地,发出刺耳的脆响。
她僵在原地,像一座瞬间冰封的雕塑。她极其缓慢地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戴着手套的右手上。那道我刚刚注意到的红色划痕,此刻在灯光下显得触目惊心。
“这……不可能……”她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彻底的迷茫与恐惧。
而我,这个飘荡的亡魂,却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我当然记得那道划痕,那是我用尽生命最后一点力气,在她手腕上留下的印记。
凶手就在眼前。
不,不对。我的意识陷入了更深的混乱。如果林若雪是凶手,她为何对自己手腕上的伤口毫无印象?她眼神里的震惊与恐惧,根本不像伪装,那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崩塌。
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杀了我。
这个念头比“她就是凶手”更让我恐惧。
解剖室的门再次被推开,刑侦支队长张启山走了进来。他是我和林若雪的大学学长。
他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林若雪,眉头紧锁。“若雪,怎么回事?”
张启山接过小刘递上的报告,迅速浏览后,脸色变得异常凝重。他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林若雪,那眼神里有怀疑,有不解,但更多的是痛惜。
“若雪,”他放缓语气,“你先停下工作,跟我回队里一趟。你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顾言的指甲里,会有你的DNA。”
林若雪的身体晃了晃。她脱下手套,露出那道清晰的划痕,眼神里充满了陌生。“我不知道……启山哥,我真的不知道……我昨晚一整晚都在局里分析卷宗……”
我飘到她身边,从她颤抖的瞳孔里找不到一丝破绽,只有纯粹的恐慌。
张启山沉默片刻,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肩上。“我知道。但程序必须走。跟我来吧。”
林若雪被带走了。解剖室里只剩下我、我的尸体,和一脸茫然的小刘。
我悬浮在自己的尸体上方,凝视着那张微笑的脸。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
脑海中闪回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死亡前那晚,我正在用AI修复一张童年合照,照片上抱着我的那个男人,脸被齐齐剪掉了。我的“父亲”。
每晚十一点准时从楼上传来的弹珠落地声。我曾用声纹采集仪分析过,结果让我毛骨悚然——那声音的频率和衰减模式,更像一颗不规则的球状骨骼在滚动。人的头骨。
还有我发布的那些关于都市传说的短视频。粉丝说我是“预言家”,因为我虚构的死亡场景,总会在几天后真实上演。最新的一个视频,讲的就是一个“微笑杀手”的故事,他会取走受害者的心脏……
视频发布时间,是我死亡前73小时。
一瞬间,所有线索像淬毒的藤蔓将我缠绕。我的死,林若雪的嫌疑,消失的心脏,楼上的头骨,没有脸的父亲,杀人预告般的视频……它们交织成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
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林若雪也不是真正的凶手。她和我一样,都只是这张网上的猎物。
那个躲在暗处的织网者,正享受着他亲手导演的戏剧。
我看着解剖台上那具没有心的躯壳,那抹微笑仿佛在对我说:
游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