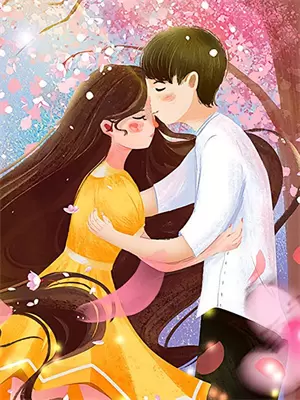我在旧书里找到他写的便签时,书店刚好亮起第三盏灯
作者: 墨玄柏其它小说连载
金牌作家“墨玄柏”的现言甜《我在旧书里找到他写的便签书店刚好亮起第三盏灯》作品已完主人公:沈知远旧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男女主角分别是旧书,沈知远的现言甜宠,大女主,爽文,甜宠,先婚后爱小说《我在旧书里找到他写的便签书店刚好亮起第三盏灯由新锐作家“墨玄柏”所故事情节跌宕起充满了悬念和惊本站阅读体验极欢迎大家阅读!本书共计55541章更新日期为2025-10-10 10:34:52。该作品目前在本完小说详情介绍:我在旧书里找到他写的便签书店刚好亮起第三盏灯
12025年春末,我在“晚灯书店”的玻璃门上贴新海报时,
巷口的快递车“嘀嘀”响了两声——是房东寄来的租金通知单,
红色印章印着“下月起租金上涨 30%”。指尖捏着薄薄的纸,风把海报吹得卷起来,
边角蹭过门框上的刻痕——那是去年冬天,常客周老师帮我修门时,随手刻的“书有光,
读照亮”。我蹲下来,把海报重新贴好,胶棒在手里转了三圈,还是没忍住红了眼眶。
晚灯书店开在老城区的青石板巷里,已经三年了。
最初是为了圆外婆的梦——她年轻时在供销社卖书,总说“要是有间自己的书店,
天黑了也亮着灯,多好”。可现在,实体书店的日子越来越难:线上书店打价格战,
纸质书销量下滑,连周老师这样的老顾客,也开始用电子书阅读器。“林老板,又贴海报啊?
”巷口裁缝店的张婶探出头,手里拿着半块刚烙好的饼,“昨天我家姑娘说,
你这儿有本《城南旧事》,她想借来看。”“有,在儿童区第三排。”我接过饼,咬了一口,
芝麻香混着眼泪的咸味,“张婶,下月租金涨了,我这店……可能要撑不下去了。
”张婶叹了口气:“这老巷里就你这书店有生气,要是关了,多可惜。对了,
前几天我侄女说,她认识个修旧书的师傅,手艺特别好,你不是收了批旧书吗?
说不定能让他看看,修好了能卖个好价钱。”我心里一动。上周确实收到一批旧书,
是一位退休教授捐赠的,其中有本 1982年版的《边城》,封面缺了角,
内页还夹着一张泛黄的信纸,字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当时我想扔了,
周老师说“旧书里藏着别人的日子,修修说不定能找到故事”。当天下午,
我按张婶给的地址,找到了“知远旧书修复工作室”。工作室在巷子深处,门是旧木的,
挂着块小牌子,上面的字是手写的:“修书如修心,慢一点,再慢一点。”推开门时,
一个男人正坐在窗边修书。他穿着浅灰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
手指捏着细如发丝的竹镊子,正在给一页破损的纸“补肉”——旧书修复里的术语,
用特制的纸浆填补缺损的部分。阳光落在他手上,连指节的弧度都透着认真。
“请问是沈知远师傅吗?”我放轻脚步,怕打扰他。男人抬头,眼睛很亮,像浸在水里的墨,
只是没什么情绪:“我是。找我修书?”我把《边城》递过去:“这本书想修一下,
还有里面的信纸,能不能尽量看清字迹?”沈知远接过书,指尖轻轻拂过封面的磨损处,
动作温柔得像在摸一件珍宝。他翻到夹着信纸的那页,眉头皱了皱:“封面用浆糊补,
内页要脱酸,信纸是宣纸材质,字迹洇得厉害,只能用特殊的显影剂,至少要一周。
”“多少钱?”我问。“这本书不收钱。”他突然抬头,目光落在我胸前的书店徽章上,
“晚灯书店?我去过,去年冬天在你那儿买过本《小王子》,你给我找了本精装版的。
”我愣了愣。去年冬天的事,我早忘了,他竟然还记得。“不过,”他话锋一转,
“我有个条件。修复期间,我要去你书店待着,看看那批旧书里有没有值得修的。
”我有点犹豫。这人看起来有点怪,话少,还对旧书格外执着。但想到书店的困境,
还是点了点头:“行,只要能修好这本书,你随时来。”他低头继续修书,
声音轻得像落在纸上的笔:“明天我过来,带我的工具。”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夕阳透过窗户,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一堆旧书上,像一幅安静的画。我突然觉得,
这老巷里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糟。2第二天一早,沈知远推着一辆旧自行车来了,
后座绑着一个木箱子,里面全是修书工具:竹镊子、马蹄刀、各种型号的浆糊刷,
还有几瓶我叫不出名字的试剂。“修书台要靠窗,光线好。”他环顾书店,
最后选了儿童区旁边的角落,“还要一张干净的桌子,不能有灰尘,旧书怕潮。
”我赶紧把靠窗的桌子收拾出来,用酒精擦了三遍。沈知远打开箱子,把工具一一摆好,
动作整齐得像在列队,连镊子的方向都要一致。“你这书店的书,摆得有点乱。”他突然说,
目光扫过文学区,“同一作者的书没放在一起,新版和旧版混着,读者找起来不方便。
”我有点不服气:“我这是按‘喜欢的程度’摆的,比如我喜欢沈从文,
就把他的书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书店是给读者开的,不是给店主的。”他语气平淡,
却像在我心上敲了一下,“你看这本《围城》,封面都磨破了,还放在最上面,
容易掉页;还有这本《朝花夕拾》,是 1979年版的,没有塑封,落了灰,会加速老化。
”我脸有点红。其实我知道这些问题,只是最近忙着愁租金,没心思管。“我帮你整理吧。
”他放下手里的镊子,开始动手。他整理书的方式很特别,先按作者分类,再按出版年份排,
旧书单独放在带玻璃门的柜子里,还在旁边贴了小卡片,写着“旧书易碎,轻拿轻放”。
周老师来的时候,看到沈知远,眼睛一亮:“这位是修书师傅吧?
我那本 1956年版的《唐诗三百首》,扉页掉了,能不能修?”沈知远接过书,
翻了翻:“可以,用线装的方式重新装订,保留原来的扉页,一周后来取。
”周老师高兴得像个孩子:“太好了!这书是我老伴年轻时送我的,她走了之后,
我就靠这本书想她。”沈知远的动作顿了顿,声音软了些:“阿姨要是知道你这么珍惜,
肯定会开心的。”那天下午,书店里很安静。沈知远修书,我整理新到的书,
偶尔有顾客进来,他也不抬头,只是在有人碰到旧书时,会轻声提醒“小心点”。快打烊时,
沈知远突然说:“你这书店,其实可以做‘旧书寄卖’。让顾客把家里的旧书拿来寄卖,
你收点佣金,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吸引更多人来。”我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
我怎么没想到?”“因为你太急了。”他收拾工具,“租金的事,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
明天我带显影剂来,试试能不能看清信纸上的字。”他走后,我按他说的,
在门口贴了“旧书寄卖”的通知。晚风穿过书店,吹得旧书的纸页“沙沙”响,我突然觉得,
那盏亮了三年的灯,好像又有了希望。3接下来的几天,沈知远每天都会来书店。
他修书的时候很专注,不说话,也不看手机,只有在我递给他温水时,会说声“谢谢”。
偶尔有顾客问他修书的事,他也会耐心解释,只是话依然不多。周三下午,
周老师带了个朋友来——也是位退休老师,姓王,手里抱着一摞旧书,说要寄卖。
其中有本 1965年版的《青春之歌》,扉页上有手写的批注,
字里行间全是年轻时的热血。“这是我当年插队时带的书,”王老师笑着说,
“那时候没什么书看,就靠这本打发时间,里面的批注都是跟我一起插队的姑娘写的,
后来她回了城,就再也没见过。”沈知远停下修书,
抬头看着王老师:“这本书的批注很有价值,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做成影印版,
说不定能找到那位姑娘。”王老师眼睛红了:“真的吗?我找了她四十年,要是能找到,
就算死也瞑目了。”那天晚上,沈知远没按时走。他帮王老师扫描批注,我帮他整理扫描件,
不知不觉就到了十点。书店的灯亮了三盏——门口一盏,收银台一盏,还有修书台那盏。
暖黄的光裹着旧书的墨香,连空气都变得温柔。“你为什么喜欢修旧书?”我忍不住问。
沈知远手里的鼠标顿了顿:“我爷爷是修书的,小时候我总在他的工作室玩,
他说‘每本旧书都有主人的温度,修好了,温度就不会散’。我爷爷走后,
我就接了他的手艺。”“那你有没有修过特别难忘的书?”“有。”他打开手机,
给我看一张照片,是本很旧的《诗经》,“这本书是我爷爷修的最后一本书,
里面夹着我奶奶写给爷爷的情书,1952年的,现在还能看清字迹。我奶奶走得早,
爷爷就靠这本书想她。”我看着照片里的情书,
突然想起《边城》里的那张信纸:“明天能修信纸了吗?我有点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嗯。”他点头,目光落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又很快移开,“早点打烊吧,
你明天还要开店。”第二天,沈知远带来了显影剂。他把信纸放在特制的玻璃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