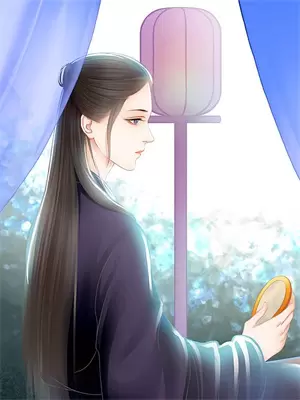我叫沈默,人如其名,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的写作事业正滑向无声的深渊。曾经,
我也拥有过名字出现在畅销书榜上的短暂辉煌,但灵感如同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干瘪下去。
接连几部作品的失败,让编辑的电话从催促变成了客套的问候,最终归于沉寂。
电脑里堆积的废稿,像一座座坟茔,埋葬着我过去的才华。于是,我选择了逃离。
逃离都市的喧嚣,逃离同行若有若无的怜悯目光,
也逃离那个在派对上被介绍为“前悬疑小说家”的尴尬身份。
这栋位于远郊、几乎被世人遗忘的百年老宅,成了我最后的避难所,也是我绝望中的赌注。
我幻想着,这沉淀了百年寂静与秘密的空间,能重新唤醒我内心沉睡的故事精灵。
老宅的确古老。斑驳的墙面爬满了枯萎的藤蔓,像垂死老人手臂上的血管。
木质结构在风中发出细微的呻吟,仿佛在诉说无人倾听的往事。
空气里弥漫着木头腐朽、灰尘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类似旧纸张和草药混合的沉闷气息。
搬进来的第一天,我站在空旷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回声的客厅里,
竟感到一种病态的契合——我的内心,同样荒凉且布满尘埃。
邻居是在我搬运最后一批书籍时出现的。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身形佝偻的老人,
悄无声息地站在篱笆的那一头,如同一棵扎根在那里的枯树。他的脸上沟壑纵横,眼神浑浊,
却像两口深井,望不见底。“又来了一个写字的?”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像砂纸摩擦着木头。我勉强笑了笑,点了点头,“嗯,来找点安静。”“安静?
”老人嘴角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嘲讽,“这里的安静,能吃人。”他顿了顿,
混浊的眼珠似乎聚焦在我脸上,“上一个,也是你们这样的。住进来的时候,眼睛里有火,
后来……火灭了,人也没了。”“没了?”我心中一动,悬疑作家的本能被勾起。
“笔杆子耍不动了,人也就废了。”老人慢悠悠地说,拐杖轻轻敲打着地面,“这房子,
挑人。”他说完,不再看我,转身蹒跚着消失在自家院落的阴影里,留下我站在原地,
心头莫名地覆上一层阴翳。当时我只将这归结为乡野老人的怪诞迷信,甚至潜意识里,
还将这视为某种可用的“素材”,那点微不足道的职业兴奋感,冲淡了最初的不安。
整理工作持续了三天。老宅比我想象的更加破败,但也更加……有“味道”。
尤其是那个位于顶层的阁楼,低矮、昏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微弱的光线。
里面堆满了不知哪个年代的杂物,覆盖着厚厚的灰尘,蛛网如同幽灵的纱幔四处悬挂。
就是在那里,在我试图清理出一个角落堆放旧书时,我的脚踢到了墙根处一块松动的木板。
鬼使神差地,我撬开了它。后面是一个黑黢黢的墙洞,不大,仅能容一只手深入。
洞里散发出一股陈腐的霉味。我摸索着,
指尖触到了一个硬硬的、用某种厚实布料包裹的物件。
那是一个用深褐色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方形物体,入手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某种重量。
油布边缘已经有些脆化,显示出岁月的痕迹。我拿着它,走下阁楼,回到相对明亮些的书房。
在书桌前,我小心翼翼地解开捆绑的细绳,层层掀开油布。里面并非印刷精美的书籍,
而是一本手工装订的册子。封面是空白的牛皮纸,没有任何标题或署名。
纸页是那种老式的稿纸,泛着不均匀的焦黄色,边缘有些卷曲破损。我深吸一口气,
翻开了第一页。字迹,是一种暗红色。不是墨水的红,更像是一种……干涸的血色,
或者某种植物汁液混合矿物形成的特殊颜料,带着一种不祥的质感。字迹本身也极不稳定,
时而狂乱潦草,笔画仿佛要挣脱纸面的束缚,
充满了压抑不住的躁动与愤怒;时而又工整得近乎刻板,一笔一划都透着一种绝望的克制。
这不像小说,更像是一本日记,或者……精神病人的呓语记录。
里面断断续续地记载着:“……三月十七,雨。窗外的树影像鬼爪,我想把它写下来,
但‘狰狞’这个词背叛了我,它变得苍白无力……”“……四月二日,晴。构思一个新角色,
一个有着琥珀色眼睛的女巫。可落笔时,眼睛只剩下‘眼睛’,琥珀色消失了,
就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色彩……”“……五月不详。它们在逃离我!形容词第一个叛逃,
接着是比喻……我的故事正在失去温度,变成冰冷的骨架……”“……末日将至。
名词也开始模糊了‘迷宫’变成了‘通道’,
‘秘密’变成了‘信息’……世界正在我笔下坍缩……”越往后翻,字迹越混乱,
那种透纸而出的绝望感也越发浓郁。
书写者显然经历着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痛苦——不是写不出的痛苦,
而是“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正在从内部瓦解的痛苦。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这描述……太诡异了。像是一种病症,一种只针对书写者的诅咒。终于,我翻到了最后一页。
这一页异常“干净”,没有前面那些混乱的涂改和癫狂的笔迹。只有一行字,
用那种暗红色的颜料,工工整整地写在页面中央,
仿佛一个最终的判决:“当文字于此地失效第七日,午夜钟鸣之时,屋中之笔者,
将被其所弑。”一股寒意,瞬间从脊椎窜上头顶。“文字失效”?“被其所弑”?这算什么?
一个疯子的临终预言?还是一个……针对后来者的警告?“屋中之笔者”——此刻,
不正是指我吗?我猛地合上册子,仿佛它烫手一般。胸腔里的心脏怦怦直跳,
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响亮。我环顾四周,熟悉的书房似乎变得有些陌生。
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原本是我知识的堡垒,此刻却像沉默的墓碑。
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暮色透过玻璃,
给房间内的所有物件都蒙上了一层暧昧不明的灰色。荒谬。这太荒谬了。我告诉自己。
一个前房客的精神崩溃记录,怎么能当真?
这世上怎么可能存在“文字失效”这种超自然现象?我将那本册子重新用油布包好,
塞进了书桌最底层的抽屉,用力关上,仿佛这样就能将那个不祥的预言也一同锁起来。然而,
那颗名为“怀疑”的种子,已经悄然落下。它在意识的土壤里潜伏着,
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最初的几天,生活似乎并无异样。我按照计划,每天坐在书桌前,
努力与空白文档搏斗。进展缓慢,思绪凝滞,但这于我而言已是常态。
老宅的寂静偶尔会被一些细微的声响打破——阁楼传来的轻响,
墙壁内部仿佛有什么东西爬过的窸窣声,夜深人静时若有若无的叹息。
我都将其归咎于老房子的自然现象,或是自己过于紧绷的神经产生的幻觉。直到第四天下午,
那最初的、细微的裂痕,出现了。那天,我正试图描写窗外庭院里那棵姿态奇崛的老槐树。
它虬结的枝干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伸展,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带着一种苍凉而执拗的美感。
我敲下键盘:“那诡异而扭曲的枝干……”手指离开回车键的瞬间,
屏幕似乎极其轻微地闪烁了一下,速度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视觉残留。但我定睛看去时,
句子变成了:“那扭曲的枝干……”“诡异”这个词,消失了。我愣住了。是我打错了?
还是……眼花了?我摇摇头,肯定是最近太累,注意力不集中了。我删掉“扭曲的”,
重新输入:“阴森的枝干……”这一次,我紧紧盯着屏幕。在敲下回车,
指尖尚未完全抬起的刹那,我清晰地看到,“阴森”两个字在屏幕上短暂地存在了零点几秒,
然后像被无形的橡皮擦抹去一样,突兀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依旧是那个干巴巴的“扭曲的枝干”。一股凉意顺着我的尾椎爬了上来。不……不可能!
我有些不信邪,甚至带着点愤怒,
快速地敲击:“狰狞的”、“如同鬼爪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每一次,
结果都一样。所有带有主观情感色彩、试图赋予对象特定氛围和属性的形容词,
都在成型的瞬间被剥离、被抹除,
只留下最基础、最客观、最不带感情 色彩的描述——“扭曲的”。不仅仅是形容词!
我尝试加入比喻:“像挣扎的囚徒的手臂”,回车后,变成了:“像手臂”。
隐喻、象征……所有修辞手法,都在失效!我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这不是卡文,
不是灵感枯竭!这是某种……强制性的“净化”!一种无形的力量,
正在粗暴地剥夺我语言中的色彩、温度和个性,将它压缩成苍白的事实陈述。我猛地站起身,
在书房里烦躁地踱步。目光扫过书架上那些文学大师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华丽辞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