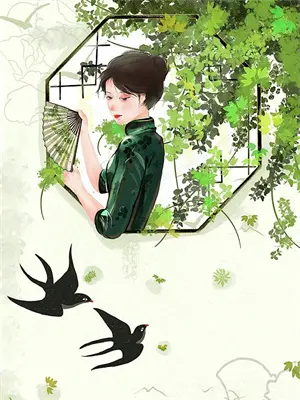
第一章林晚第一次见到沈牧的律师时,手里攥着的诊断书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似乎还顽固地黏在她的头发和衣服上,
与眼前这间宽敞明亮、能俯瞰大半个城市景观的律师办公室格格不入。巨大的落地窗外,
初夏的阳光给钢筋水泥的森林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除了她此刻沉入谷底的心。“林女士,这是沈牧先生委托我提交给您的离婚协议草案,
请您过目。”戴着金丝边眼镜、一丝不苟的王律师将一份装订精美的文件轻轻推到她面前,
语气平和,不带任何个人感情,仿佛在讨论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商业合同。
林晚没有立刻去碰那份文件。她的目光落在自己放在膝头的手上,这双手,
曾经也被称赞过纤细白皙,如今指节处却有了常年操劳留下的细微痕迹,皮肤也粗糙了些。
十年婚姻,她把这双手浸泡在洗洁精、洗衣液和油腻的洗碗水里,把心血熬进一粥一饭,
把青春铺陈在这个名为“家”的方寸之地。而沈牧,她法律上的丈夫,
此刻不知在地球另一端的哪个商务酒会上侃侃而谈,
派来的只是一个代表他冰冷意志的陌生人。她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想从这充满昂贵香水味和权力感的空气里汲取一点勇气,然后才伸出手,
翻开了那份决定她未来命运的文件。条款清晰,措辞严谨,
充分体现了沈牧一贯的行事风格——高效、冷静,不留余地。关于财产分割,
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位于城西那套老旧的两居室公寓归她,那是他们结婚时的婚房,
随着沈牧生意越做越大,他们早已搬离;一辆车龄超过五年的代步车归她;以及,
一笔五十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补偿金”三个字,像根细小的针,轻轻扎了她一下。
补偿什么?补偿她十年付出的感情?补偿她因照顾家庭而中断的职业生涯?
还是补偿她此刻口袋里那张写着“疑似恶性肿瘤,需进一步检查”的诊断书?
王律师似乎看出了她的恍惚,轻轻咳嗽一声,补充道:“林女士,
沈先生考虑到您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这五十万是他在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之外,
额外给予您的一笔钱,希望能帮助您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好聚好散。” 好聚好散。
林晚在心里默念着这四个字,嘴角扯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苦涩弧度。
他连最后的面纱都要撕得如此彻底,用一笔钱来买断过去的一切,
包括她可能存在的任何纠缠。见她沉默,王律师又推过来一张支票,
金额处清晰地写着:伍拾万元整。“沈先生交代,如果您对协议没有异议,签完字,
这笔钱您可以立刻兑现。”林晚的指尖冰凉。她需要钱,迫切需要。
医生的建议是尽快住院进行深入检查和手术,后续的治疗费用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她心头。
那套老房子是她唯一的栖身之所,不能卖。这五十万,也许是她的救命钱。尊严和生存,
在这个瞬间被赤裸裸地放在天平两端。她想起半个月前,她难得拨通那个越洋电话,
想告诉他自己的身体可能出了严重问题,电话那头的背景音是喧闹的音乐和酒杯碰撞声,
沈牧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和醉意:“晚晚,我这边正忙,有个重要客户。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听话。” 然后便是忙音。那一刻,她就该明白,她在这场婚姻里,
早已成了那个不被需要的、可以随时被打发的“事”。“林女士?
”王律师的催促将她从回忆里拉回。林晚抬起头,看着律师那双洞察世事却毫无温情的眼睛,
缓缓地、清晰地说:“协议我看了。房子和车,我接受。但这五十万补偿金,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我不要。
”王律师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真正的惊讶,这在他专业的面具上是极少出现的神情。
“林女士,您确定吗?这是沈先生的一片心意,而且,这对您目前的情况……”他话没说完,
但意思明显,或许沈牧连她生病的事也早已知道,
这笔钱带着某种“封口”或“彻底了断”的意味。“我确定。”林晚的声音不大,
却异常坚定,“既然要断,就断得干净一点。这十年来,我付出的是感情和时间,
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劳务。他的钱,还是留着他去拓展他的商业版图吧。”说出这番话,
她感到一种虚脱般的轻松,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茫然。拒绝了这笔救命的钱,
她的未来在哪里?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自尊,
让她无法接受这种带有施舍和买断性质的“补偿”。她可以失去婚姻,失去健康,
但不能连最后一点对自己过往付出的尊重都丢掉。王律师显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调整了一下领带,试图挽回:“林女士,我建议您再慎重考虑一下。
情绪化的决定往往……”“我不是情绪化。”林晚打断他,拿起桌上的笔,翻到协议签名处,
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吧。麻烦您转告沈牧,我祝他前程似锦。”她站起身,
脊背挺得笔直,没有再去看那张轻飘飘却重如千钧的支票。走出气派的办公楼,
初夏的阳光有些刺眼,她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周围行色匆匆的人群,
第一次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孤独。口袋里的诊断书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她的皮肤。
她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市中心公园。坐在熟悉的长椅上,这里是她过去十年里,
每次和沈牧争吵或感到压抑时,独自舔舐伤口的地方。曾经,他们也会在周末的傍晚,
像普通情侣一样在这里散步,那时沈牧还会牵着她的手,
指着远处的楼盘说将来要买那里的大房子给她住。物是人非。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不是为失去的婚姻,而是为这十年被辜负的时光和此刻岌岌可危的健康。她哭得悄无声息,
肩膀微微颤抖,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不知过了多久,一双穿着老旧布鞋的脚停在她面前。
林晚抬起头,泪眼模糊中,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穿着朴素但十分干净的老太太,
正关切地看着她。老太太递过来一张干净的手帕,
是那种很老式的、带着淡淡肥皂香的白手帕。“姑娘,擦擦吧。天大的事儿,
哭完了也得想办法不是?”老太太的声音温和而慈祥。或许是压抑太久,
或许是老太太的善意触动了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林晚竟对着一个陌生人产生了一种倾诉的欲望。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处境,
失败的婚姻,可怕的病情,以及刚刚被她拒绝的那笔“买断费”。老太太安静地听着,
没有打断,也没有过多的安慰,只是时不时点点头。等林晚说完,她才缓缓开口:“姑娘,
你做得对。人的脊梁骨,有时候比命还重要。钱没了可以再挣,脊梁弯了,
一辈子就直不起来了。”老太太的话像一道光,照进了林晚黑暗的心底。她看着老太太,
虽然年迈,但眼神清亮,透着一股经历过风霜后的从容和坚韧。
“可是……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可能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了……”林晚茫然地问。
老太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随身带着的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
拿出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牛皮笔记本,本子的边角已经磨损,但保存得很完好。“我姓苏,
以前是学经济的,也经历过不少起落。这里面的东西,是我一辈子攒下的一点心得,
关于怎么用有限的资源,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老了,用不上了,看你是个有骨气的孩子,
送给你吧。或许能帮你走几步路。”林晚愣住了,连忙推辞:“苏奶奶,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拿着吧。”苏奶奶不由分说地把笔记本塞进林晚手里,“知识这东西,
分享出去才有价值。记住,越是没人看好你的时候,越要看得起自己。日子还长着呢。
”苏奶奶拍了拍她的手,站起身,步履蹒跚却稳健地离开了。林晚握着那本沉甸甸的笔记本,
看着老太太远去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这突如其来的善意,像严冬里的一簇火苗,
虽然微弱,却让她感到了一丝暖意。她打开笔记本,
扉页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致每一个在谷底仰望星空的人。
”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和图表,有些是剪报贴上去的,
涉及经济周期、资产配置、甚至还有一些对未来行业趋势的判断,笔迹从青涩到苍劲,
跨越了很长的时间。林晚的心,第一次因为婚姻和病痛之外的東西,剧烈地跳动起来。
她隐约感觉到,这本看似普通的笔记本,或许真的蕴含着改变命运的力量。她擦干眼泪,
将诊断书折好,紧紧攥着笔记本,站起身。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孤独依旧,
但那份深入骨髓的绝望,似乎被注入了一丝微弱的、名为“希望”的力量。
她不知道前方等着她的是什么,是更艰难的治疗,还是孤独的挣扎,但至少,
她为自己守住了一点什么。这点东西,此刻,比五十万,更让她觉得踏实。
第二章医院的走廊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无形的焦虑混合的味道。
林晚独自坐在冰凉的金属长椅上,等待着叫号。她手里紧握着苏奶奶给的那个笔记本,
仿佛那是能给她带来力量和运气的护身符。过去几天,
她几乎是不眠不休地研读了里面的内容。起初,那些经济术语和曲线图让她头晕眼花,
但慢慢地,她仿佛能触摸到苏奶奶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思考和智慧。
笔记本里不仅有理性的分析,还有苏奶奶本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做出人生选择的心路历程,
像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在对她娓娓道来。“林晚!”护士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沉思。
她深吸一口气,走进诊室。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情况比初诊时预想的更复杂,
肿瘤的位置有些棘手,主治医生是一位表情严肃的中年女教授,姓陈。
陈教授看着她的各项报告,眉头微蹙:“林女士,你的情况,手术是必要的,但有一定风险。
而且术后根据病理结果,可能还需要进行放化疗,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周期会很长。
你的家人……”“我自己可以做决定。”林晚平静地打断她,声音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镇定,
“陈教授,请安排手术吧,费用的问题,我会想办法。”陈教授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
似乎想从她苍白的脸上找出逞强的痕迹,但只看到了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平静。
她点了点头:“好,那我们就尽快安排。你先去办住院手续,预付一部分费用。
”预付的金额对此时的林晚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
她拿出了工作这些年偷偷攒下的一点微薄积蓄,那是准备等沈牧生意稳定些,
她重新出去找工作时的过渡资金,如今看来是杯水车薪。她想到了那套老房子,
那是她最后的堡垒。她联系了中介,得到的评估价并不高,而且卖房需要时间,
她的病等不起。晚上,躺在临时租住的、条件简陋的单人间里为了凑钱,
她已将老房子挂出,并暂时搬了出来,林晚再次翻开了苏奶奶的笔记本。其中一页,
苏奶奶用红笔标注了一段话:“危机二字,危中有机。对于一无所有的人,
机会在于‘低买’。在普遍恐慌时,寻找被极度低估的资产,需要的不是资金,
是眼光和胆量。”被极度低估的资产……林晚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她有什么?
她几乎一无所有。除了那笔她拒绝了的五十万,以及……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从床底拖出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那是她清理婚房时,带出来的属于她个人的一些杂物。
箱底,安静地躺着一张有些褪色的股权证书。那是十年前,
沈牧刚刚创立他的“牧野科技”时,为了表达与妻子共同奋斗的决心,
也是公司初创亟需资金,他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将公司5%的原始股,记在了林晚名下。
当时,牧野科技还只是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工作室,这5%的股份,形同废纸,甚至不如废纸,
因为它还意味着潜在的债务风险。沈牧后来事业蒸蒸日上,多次增资扩股,
这5%的股份早已被稀释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恐怕连沈牧自己都忘了这回事。
在离婚协议里,关于牧野科技的资产,只字未提,显然,在沈牧和他律师的认知里,
这早已不属于需要分割的财产。林晚拿着这张轻飘飘的纸,心脏却怦怦直跳。
她打开那台卡顿不堪的旧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一切关于“牧野科技”的信息。十年时间,
沈牧确实展现了他的商业才华,牧野科技已经从当初的小工作室,
发展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几年前还成功在创业板上市了!
虽然市值不算顶尖,但也是一家正经的上市公司。她找到牧野科技的股价走势图,
曲线起伏跌宕。最近半年,因为行业竞争加剧,公司推出的新一代产品市场反响不及预期,
股价正处于持续下跌的低谷期。林晚根据股权证书上的信息,粗略估算了一下,
这被遗忘的5%原始股,经过多次稀释和拆股后,对应的现有股份价值,
大概在二三十万左右。这笔钱,不足以覆盖她全部的治疗费用,
但足以支付手术的预付和前期部分治疗。她该卖掉吗?立刻套现,解燃眉之急。
这是最直接的想法。但苏奶奶笔记本里的话,和她研究股价走势时看到的那种“低估”状态,
让她产生了一丝犹豫。卖掉,就是彻底的断了。这点股份,
是那段婚姻留给她唯一的、不带施舍色彩的东西,是十年前那个还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沈牧,
给予妻子的承诺的物证。更重要的是,如果公司未来能走出低谷呢?
她知道自己这个想法很大胆,甚至有些冒险,对于她这样一个对金融市场一无所知的人来说,
这更像是一场堵伯。她想起了苏奶奶在另一页写下的批注:“投资,最终是投人。
即便对象是一家公司,也要看掌舵者的心性和能力。” 沈牧的能力,她从不怀疑,
他有野心,有手腕,能抓住机会。但他的心性……林晚闭上眼,
离婚前后他那冰冷的处理方式,让她心寒。这样一个在感情上可以如此利落割舍的人,
在商场上,会是一个有韧性、能带领公司穿越低谷的掌舵者吗?她不确定。
内心的挣扎持续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她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做出了决定。
她联系了陈教授,请求将手术时间尽量后延一段时间,给她一点筹措资金的空间。
陈教授虽然不解,但看她态度坚决,还是答应了,但严肃告诫她病情不能拖延太久。然后,
林晚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她没有卖掉那点微不足道的股份,
而是用她几乎所有的积蓄,加上用老房子做抵押贷来的一小笔钱,
在牧野科技的股价跌至历史低点附近时,悄悄地、分批买入了更多股票。这个举动,
在她当时所有的亲友看来,无疑是疯了。用一个即将做癌症手术的人的全部家当,
去赌一家前景不明、且前夫所在的公司的股票上涨?但林晚有自己的逻辑。
这逻辑一部分来自于苏奶奶笔记里对智能家居行业长期前景的判断,
一部分来自于她对沈牧商业能力的了解尽管情感上已破裂,但她理性上承认他的能力,
还有一部分,是一种极其微妙的、连她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心理——她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与自己的过去做一个了结,或者说,进行一次无声的对话。
她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林晚,她要主动介入,哪怕是用这种看似荒谬的方式。
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后,她的账户几乎清零,而持有的牧野科技股票,价值达到了近八十万。
她将这些股票牢牢握在手里,然后拿着抵押房子换来的一点现金,平静地走进了医院,
准备迎接她的手术。进入手术室前,她给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发了一条短信,
设置了股价预警线。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她知道,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却主动的路。
麻药注入身体,意识逐渐模糊的那一刻,她想的不是生死,
而是苏奶奶笔记本扉页上的那句话:“致每一个在谷底仰望星空的人。” 她正在谷底,
而她购买的这些股票,成了她仰望星空时,看到的几颗微弱却坚定的星。
第三章手术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陈教授技术精湛,肿瘤被完整切除,
后续的病理分析结果也比预想的要好,属于中期偏早,
这意味着后续的化疗周期可以适当缩短,预后也相对乐观。然而,
化疗的痛苦依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脱发、呕吐、浑身剧痛、免疫力急剧下降……林晚一个人租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小房子里,
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她没有告诉老家的父母,怕他们年事已高,承受不住。曾经的朋友,
也因多年疏于联系而难以开口求助。沈牧那边,更是杳无音讯,
仿佛她从他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了一般。最艰难的时候,是呕吐到几乎虚脱,
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是夜里因为疼痛和恐惧彻夜难眠,
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但她一次也没有哭。她咬着牙,
一遍遍地看着苏奶奶的笔记本,看里面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看那些起起落落的曲线图,
仿佛能从这种宏观的波动中找到一种对抗个人微观痛苦的力量。她开始自学金融知识,
在网上搜索资料,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自己那个看似冲动的决定。她开设了一个网络博客,
匿名记录自己的抗癌历程和学习投资的心得。她没有透露任何真实信息,
只是用一种冷静甚至略带抽离的笔触,描述身体的痛苦、内心的迷茫,
以及试图从宏观经济和公司财报中寻找规律时获得的片刻宁静。
她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化疗是刮骨疗毒式的重组,而坚持下去的信念,
则是潜在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奇特的比喻和真实的情感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