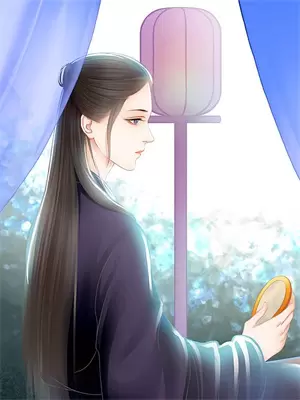1 渔港血誓2010 年秋,滨江国际港口论坛的鎏金拱门还沾着晨露。
赵晓敬站在铺着红绒的发言台后,海风掀起他定制西装的下摆,
麦克风里传出抑扬顿挫的宣言:“三年内,
让我们的码头成为东南亚航运枢纽 ——”掌声如潮时,穿藏青工装的男人挤过警戒线。
他胸前别着伪造的工作人员证件,右手藏在背后,当赵晓敬伸手致意的瞬间,男人扑上前,
三记寒光闪过 —— 船用匕首的三棱刃口精准刺入胸腔。“郑文强!” 有人认出刺客。
男人没有逃跑,任由保安按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视线越过混乱的人群,
望向港口方向的集装箱吊臂,嘴角竟扯出丝笑意。警方到场时,
他只对刑警们重复一句话:“私人恩怨,我认。”滨江市晚报的热线电话炸响时,
马世杰正在改一篇渔港污染的深度稿。“马记者…… 赵副市长遇刺了!
” 编辑的声音带着颤音,他手里的钢笔 “啪” 地砸在稿纸上,蓝墨水晕开像片微型海。
殡仪馆的冷柜前,林倩的哭声碎得像浪花。她穿着黑色套裙,
指甲缝里还嵌着未洗净的白菊汁液,看见马世杰便扑过来抓住他的胳膊:“大哥,
文强他怎么敢……” 话没说完就被泪水噎住,睫毛上的泪珠折射着冷光灯,
眼神却像蒙了雾的渔港,藏着说不清的东西。马世杰掀开白布,
赵晓敬胸口的缝合线狰狞如蛇,那张曾在酒桌上笑出褶子的脸,此刻苍白得没有一丝生气。
拘留所的会见室隔着厚玻璃。郑文强比十天前瘦了一圈,颧骨凸起如礁石,
眼神死寂得像废弃码头的深潭。“为什么?” 马世杰把录音笔推到玻璃边,
指尖因用力而发白。“大哥,我对不起你。” 郑文强的声音沙哑,喉结滚动了两下,
“但赵晓敬必须死。”“当年歃血为盟的话都忘了?” 马世杰猛地拍向桌面,
玻璃震出细碎的嗡鸣。郑文强却别过脸,望着窗外铁丝网外的天空,再也不肯开口。临走时,
马世杰看见他手腕上的旧疤 —— 那是 2000 年替赵晓敬挡刀留下的,
三道划痕像褪色的船锚。老陈在刑侦大队的走廊里抽烟,烟雾缭绕中把卷宗拍在马世杰手里。
“刺杀干净得过分,匕首是船用三棱刺,黑市上都少见。” 老刑警的眉头拧成结,
“上面催着结案,说是个人报复。” 卷宗里的现场照片里,
匕首柄上刻着个模糊的 “鸥” 字,马世杰的呼吸骤然停滞。深夜整理赵晓敬的遗物时,
书房最底层的抽屉里露出个铁盒。盒面刻着艘小木船,
船帆处的刻痕还留着当年的稚嫩 —— 那是三人在海边捡的废铁,
郑文强用凿子一下下刻出来的。锁扣早已生锈,马世杰找了把螺丝刀撬开,
里面掉出张泛黄的照片:2000 年的渔港码头,三个少年光着膀子站在渔船旁,
赵晓敬举着啤酒瓶,郑文强搂着他的肩,自己则在中间笑着,背景是翻涌的墨色海浪。
照片下压着本牛皮封面的日记,最后一页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辨认不清,
墨水洇开像干涸的血:“‘锚’已沉底,再无回头路……”马世杰的指腹抚过刻痕,
突然想起 2000 年那个暴雨夜。当地混混抢郑文强的工钱,赵晓敬突然把他拽到身后,
冲郑文强使了个眼色 —— 后者抄起码头的木杠子就冲上去,
而他攥着拳头喊 “有话好好说”,却被赵晓敬骂了句 “书呆子”。那时的海风里,
只有少年意气,没有后来的血污。铁盒最底层,还藏着半枚锈蚀的船用铆钉。
2 锈钉秘语马世杰把那枚锈蚀的船用铆钉攥在手心时,指腹能摸到钉帽边缘凹凸的纹路。
凌晨三点的书房里,台灯把铆钉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蜷在桌面的铁蛇。
他翻开赵晓敬的日记,从最后一页往前倒翻,
牛皮封面被手指磨出细碎的毛边 —— 前几十页全是官场应酬的流水账,
今天陪某领导视察,明天参加某项目奠基,直到 2008 年 7 月的那一页,
字迹突然变得潦草:“老周那边压不住了,‘锚’的接缝处得再填点东西。
”“老周” 是谁?“接缝处” 又指什么?马世杰把日记拍在桌上,起身走到窗边。
滨江的夜雾裹着咸腥气飘进来,远处码头的吊臂像沉默的巨人,在夜色里投下狰狞的剪影。
他想起老陈说的 “匕首上刻着‘鸥’字”,突然抓起外套 —— 滨江渔港的老船工里,
有个叫周福生的,年轻时在 “海鸥号” 上当过轮机长,或许能认出这铆钉的来历。
天刚蒙蒙亮,马世杰就骑着摩托车往渔港赶。沿海公路的护栏上还挂着露水,
风里混着鱼腥味和柴油味。渔港入口的老樟树下,周福生正蹲在地上补渔网,
银白的胡须上沾着碎冰,手里的梭子穿来穿去,网眼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周伯,
您看看这个。” 马世杰把铆钉递过去。老人放下梭子,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
对着光转了转铆钉,突然 “咦” 了一声,
指腹在钉帽的锈迹里抠了抠:“这是船用的高强度铆钉,只有万吨级以上的货轮才用。
你看这凹槽 ——” 他指着钉帽边缘的三道刻痕,“是‘东海船厂’的标记,
2005 年以后就停产了。”“2005 年?” 马世杰心里一紧,
“您还记得当年有哪些船用了这种铆钉?”周福生眯起眼,往海里啐了口唾沫:“还能有谁?
‘滨江 1 号’呗。那船当年是赵晓敬牵头造的,说是要搞什么‘港口振兴计划’,
结果下水没半年就沉了,还死了三个水手。”马世杰的心脏猛地往下沉。他记起来了,
2006 年夏天,滨江晚报确实登过 “滨江 1 号” 沉船的短讯,
说是遭遇台风失事,理赔很快就结束了,当时他还在跑社会新闻,想跟进却被编辑压了下来,
说 “上面打过招呼,别多问”。“那三个水手……” 马世杰的声音有些发颤。
“还能怎样?” 周福生叹了口气,重新拿起梭子,“都是咱们渔港的人,最小的才二十岁。
家属闹过一阵子,后来突然就不闹了,听说拿了不少钱。” 老人顿了顿,突然抬头看他,
眼神里带着警惕,“你问这个干啥?赵晓敬都死了,那事早该烂在海里了。
”马世杰还想再问,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林倩。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哭腔,
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慌张:“大哥,你快来家里一趟,晓敬的书房被人翻了!
”赵晓敬家在滨江新区的高档小区,保安见了马世杰却拦着不让进,说 “林女士交代过,
没她的允许谁也不能进”。直到林倩踩着高跟鞋跑过来,脸色苍白得像张纸,
抓着他的胳膊往楼上拽:“你看,抽屉全被拉开了,晓敬的文件少了好多。
”书房里一片狼藉,书架上的书散落在地,办公桌的抽屉被撬得变形,
赵晓敬生前常用的钢笔断在地上,墨水流得满地都是。马世杰蹲下来,
看着抽屉里残留的碎纸,突然注意到桌腿内侧贴着个微型录音笔 —— 藏得很隐蔽,
若不是抽屉被撬变形,根本看不见。他趁林倩收拾碎纸的功夫,悄悄把录音笔揣进兜里。
走到门口时,林倩突然拉住他的手腕,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大哥,别再查了。
晓敬已经死了,文强也进去了,咱们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行不行?” 她的眼睛红红的,
却没有眼泪,像是在哀求,又像是在警告。马世杰看着她,
突然想起 2003 年的那个春天。那时林倩还是渔港医院的护士,
赵晓敬刚当上区发改委的科员,第一次带她来见自己和郑文强。在海边的小饭馆里,
林倩穿着白大褂,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给他们倒啤酒时,手还会紧张得发抖。可现在,
她的眼神里全是马世杰看不懂的东西,像深不见底的海。“我得知道真相。
” 马世杰轻轻挣开她的手,“不光为了晓敬和文强,
也为了当年死在‘滨江 1 号’上的人。”离开小区后,马世杰找了个僻静的咖啡馆,
插上耳机听录音笔里的内容。大部分是赵晓敬和官员的对话,
全是些项目审批、资金划拨的官话,直到最后一段,录音的背景里有海浪声,
赵晓敬的声音带着酒气,还有点害怕:“‘锚’计划不能停,
那笔钱已经挪出去了…… 老周要是敢说出去,就让他跟‘滨江 1 号’一样沉到海里!
”“老周” 果然是周福生!马世杰立刻往渔港赶,可刚到樟树下,
就看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把周福生往面包车上拽。老人挣扎着喊:“马记者,他们要沉了我!
” 可没等马世杰冲过去,面包车就扬尘而去,地上只留下周福生补了一半的渔网,
网眼里还挂着条小海鱼,在阳光下徒劳地蹦跳。马世杰掏出手机想报警,
却发现屏幕碎了 —— 刚才在小区门口被保安推搡时,手机掉在地上他都没注意。
他咬着牙往老陈的刑侦大队跑,可到了门口,却被值班警察拦在外面:“陈队被停职了,
说是违规泄露案情。上面说了,郑文强的案子已经结了,谁再查就是跟市局对着干。
”马世杰站在刑侦大队的门口,看着墙上 “执法为民” 的牌子,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他想起郑文强在拘留所里的眼神,想起赵晓敬日记里的 “锚已沉底”,
想起周福生被拽走时的呼喊 —— 这些碎片像散落在海里的浮标,隐约连成一条线,
可线的另一端,却藏在更深、更黑的海里。3 潮涌旧忆那天晚上,马世杰没回家,
而是去了渔港的旧仓库。这里是他、赵晓敬和郑文强年轻时的秘密基地,
墙上还留着他们用红漆写的 “兄弟同心”,只是现在漆皮剥落,字迹模糊得像哭花的脸。
他坐在一堆旧渔网里,从背包里掏出那张泛黄的照片 ——2000 年的夏天,
三个少年光着膀子站在渔船旁,赵晓敬举着啤酒瓶,郑文强搂着他的肩,自己则在中间笑着,
背景是翻涌的墨色海浪。照片里的郑文强,左胳膊上还没有那道疤。
那道疤是 2003 年留下的。那年冬天,赵晓敬刚进发改委,负责渔港的拆迁项目。
有个叫李老栓的渔民不肯搬,说那房子是他爹传下来的,要拆就先拆了他。
开发商雇了些混混,晚上拿着棍子去砸李老栓的门,赵晓敬正好撞见,想上去拦,
却被混混推搡在地。郑文强当时在码头当搬运工,听说赵晓敬被欺负,
抄起根钢管就冲了过去,混混们掏出刀,他就用胳膊挡,结果被划了三道口子,
血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他的工装。马世杰当时在报社实习,听说这事赶过去时,
郑文强正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缝针,赵晓敬蹲在他旁边,手里攥着沾满血的纸巾,
眼睛红红的:“文强,谢了。以后我发达了,肯定不会忘了你。” 郑文强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小虎牙:“说啥呢,咱们是兄弟。”可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就变了。
赵晓敬越来越忙,陪他们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见面,说的不是项目就是领导。
2005 年春天,赵晓敬找他们俩吃饭,说要搞 “滨江 1 号” 货轮项目,
让郑文强去船上当水手长,月薪是码头搬运工的三倍。
郑文强当时犹豫了 —— 他娘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可赵晓敬拍着胸脯说:“文强,
你跟我干,以后我让你娘住最好的医院,吃最好的药。”马世杰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私下劝郑文强:“赵晓敬现在满脑子都是项目,你别太信他。
” 可郑文强却摇了摇头:“大哥,晓敬是为了咱们好。你看他现在混得多好,
以后咱们也能跟着沾光。”“滨江 1 号” 下水那天,赵晓敬请了好多领导,
在码头上摆了十几桌酒。郑文强穿着新的水手服,站在船舷边,笑得特别开心,
给马世杰敬酒时说:“大哥,你看这船,多气派!以后我就能在这上面挣钱,给我娘治病了。
” 马世杰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却被赵晓敬打断:“世杰,你别总皱着眉头,
咱们兄弟三个,以后肯定能在滨江闯出一片天。”可谁也没想到,半年后,
“滨江 1 号” 就沉了。那天马世杰正在报社写稿,突然接到郑文强的电话,
声音里全是哭腔:“大哥,船沉了!李哥他们三个都没上来!” 马世杰赶到渔港时,
海面上还飘着油污,救援船在来回搜救,郑文强坐在码头的石头上,浑身湿透,
脸上全是泪水和海水,看见马世杰就扑过来:“是我不好,
我没看好他们……”后来官方说是台风失事,可马世杰去采访时,
有个老水手偷偷告诉他:“哪是什么台风?那船的钢板薄得像纸,铆钉都是次品,
不出事才怪!” 马世杰想写报道,却被主编压了下来:“赵晓敬现在是重点培养对象,
这事不能报。” 马世杰去找赵晓敬,想问清楚,可赵晓敬却避而不见,
只让秘书传话说:“文强已经拿到抚恤金了,这事到此为止。”从那以后,郑文强就变了。
他辞了水手的工作,去了码头的修理厂,每天沉默寡言,喝酒喝到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