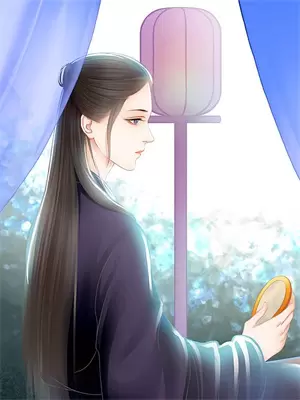1 河新娘的诅咒晚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和腐烂水草的咸腥气,钻进鼻腔。
我站在岸边,望着底下墨绿色、几乎凝滞的河水,岸边的淤泥被晒了一天,
正散发出最后一点稀薄的热气。阿姐就是在这里,消失的。镇上的老人,
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蹲在歪脖子柳树下抽烟,烟锅一明一灭。“是河新娘,
”他吐出一口辛辣的烟雾,混着水汽,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选了替身喽。
”我不信。阿姐是外来写生的学生,活泼,明亮,
跟这个沉闷腐朽、终年被水汽笼罩的小镇格格不入。她怎么会成为什么狗屁河新娘的替身。
但自从她不见后,这临河租住的老屋,深夜总能听见歌声。不是从门外,也不是窗外,
那声音飘忽不定,像浸透了河水,湿漉漉、凉丝丝地,直接钻进耳膜。是阿姐的声音,
哼着那首她最喜欢的民谣小调,只是断断续续,带着一种空洞的回响,
仿佛隔着很远的水域传来。每次我猛地坐起,浑身冷汗,那歌声就停了,
只剩下河水永无休止的、单调的拍岸声,一下,又一下。镇民们看我的眼神也怪。
带着一种混合了畏惧、怜悯,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催促。好像我留在这里,
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时宜。我问遍了所有可能见过阿姐的人,
得到的只有闪烁其词和统一的沉默。
直到那个脸上褶子像干涸河床、眼神却异常精明的喜婆找上门。她穿着一身褪色的红布褂,
站在我门口,挡住了外面灰白的天光。“想找你姐?”她上下打量我,
目光锐利得让人不舒服,“明天河新娘送亲,缺个打幡的,你来。”我没问为什么找我,
一个明显的外来人。我像是抓住了唯一一根漂浮的稻草,哪怕它通向的是更深的漩涡。
送亲的队伍,没有丝毫喜庆。天蒙蒙亮,镇子还陷在湿冷的雾气里,一行人影影绰绰,
穿着暗色的衣服,沉默地聚集在河边。没有吹打,没有喧哗,
只有脚步踩在潮湿石板和泥土上的噗呲声,压抑得让人心慌。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甜腻中带着腐朽的香火味,
是队伍前面人手里捧着的长明灯散发出来的。我跟在队伍中段,
手里攥着那根冰冷的、糊着白纸的幡杆,纸幡在静止的空气中纹丝不动。我的位置,
能清晰地看到前面四个人抬着的那顶花轿。轿子是大红色的,但那红陈旧不堪,
被水汽和岁月侵蚀得发暗,像凝固的血块。轿帘低垂,密不透风。
但随着轿夫僵硬的步伐起伏,轿帘偶尔被震开一丝缝隙。借着那惨白长明灯的光,
我瞥见里面坐着的身影。凤冠霞帔,是纸扎的。惨白的脸颊上,
涂着两团鲜艳得过分的圆形腮红,嘴唇一点朱红,弯成一个固定不变的、诡异的笑。
一双描画出来的黑漆漆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那是个纸人!
冰凉的寒意瞬间沿着我的脊椎爬上来。队伍行到河滩最平坦的一处,停了下来。面对着的,
是那条吞没了阿姐的、沉默的墨绿色大河。雾气在水面翻滚,更浓了。喜婆走到轿前,
她那身褪色红衣在灰蒙蒙的天地间,刺眼得像个烙印。她没看轿子,却缓缓地,极其缓慢地,
扭过头来。她的脖颈发出细微的“咔哒”声,像是生锈的合页在转动。她的脸正对着我,
脸上是那种仪式化的、毫无温度的假笑,嘴角咧开的弧度,竟与轿中纸人有几分相似。
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黏稠的雾气,钻进我耳朵里:“你姐姐等这个位置,
已经等了三十年。”一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凿子,狠狠楔进我的脑海。三十年?
阿姐今年才二十二!荒谬和极致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让我浑身僵直,几乎无法呼吸。
就在我心神俱震,几乎要瘫软下去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低下头,
视线落向那顶血红色的花轿。轿帘不知何时,被掀开了一角。一只惨白的手,
从轿里伸了出来。那不是活人的手,没有血色,没有温度,是用粗糙的纸张糊成的,
关节处是细密的竹篾骨架轮廓。此刻,这只纸扎的手,正紧紧地,
紧紧地攥着我白色T恤的衣角。五指收拢,将那一小块布料抓出了狰狞的褶皱。
它是什么时候……我顺着那只僵硬的手臂,一点点抬起视线,对上了轿子里那张脸。
纸人新娘那描画的黑瞳,不知何时,已经转向了我。腮红艳丽,朱唇微勾。它在“看”着我。
河风在此刻毫无征兆地变大,吹得我手中的纸幡猎猎作响,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那只纸手攥住我衣角的触感,透过薄薄的棉质T恤,
传来一种诡异的、混合着纸张粗糙和竹篾硬冷的凉意,没有活物的温度和弹性,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猛地一抽身,想挣脱,但那纸手纹丝不动,反而因为我的动作,
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纸张摩擦声。它牢牢地钉在那里,
像是从我衣角里生长出来的一部分。心脏在胸腔里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我抬起头,
视线越过那只诡异的手,撞进轿子里。纸人新娘那张惨白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
似乎更清晰了。描画的黑瞳,不再是空洞地望着前方,而是确确实实地,
向下倾斜了一个微小的角度,正正地“落”在我被攥住的衣角上,
以及我因为惊骇而僵硬的身体。那两团鲜艳的腮红,在死白的底色上,像两滴将凝未凝的血。
朱砂点的嘴唇,弯着的弧度没有丝毫改变,但那固定的笑容在此刻看来,
充满了嘲弄和冰冷的恶意。周围的送亲队伍,依旧沉默。2 纸手惊魂他们像是泥塑木雕,
对眼前这超乎常理的一幕视若无睹。捧着长明灯的,佝偻着背;抬着轿子的,
保持着僵硬的姿势;就连站在轿前的喜婆,也维持着那诡异的假笑,
仿佛我衣角上多了一只来自冥婚花轿的纸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有河风,吹得更急了,
带着尖锐的呼啸,卷起河滩上的沙砾,打在脸上,微微的疼。那风穿过纸幡,
呜咽声变成了凄厉的尖啸,像是在为这场荒诞的仪式伴奏。喜婆朝前迈了一步,
她的绣花鞋踩在潮湿的河滩碎石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她伸出手,
那只布满老年斑、皮肤像干枯树皮的手,并没有去碰触那只纸手,而是轻轻地,
搭在了我的手腕上。她的手指冰凉,比那纸手好不了多少,
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属于坟墓的寒意。“时辰到了,”她的声音平平板板,
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像是在念一句古老的咒语,“新娘该上轿了。”上轿?谁上轿?
我猛地看向她,想从她浑浊的眼珠里找到一丝玩笑或者疯狂的痕迹,但没有,
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以及深处一丝不容置疑的笃定。“不……”我喉咙发紧,
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试图甩开她的手,甩开那攥住我衣角的纸手。但喜婆的手像铁箍一样,
纹丝不动。她的力量大得惊人。就在这时,轿帘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掀开。
我看清了轿子内部。里面空间狭小,除了那个穿着纸嫁衣的“新娘”,空无一物。
但在那纸新娘的脚边,放着一双小巧的、同样是纸扎的红色绣花鞋。而在那双鞋的旁边,
安静地躺着一枚银色的、造型简单的尾戒。那是我阿姐的尾戒!她从不离身!
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迅速褪去,留下彻骨的冰寒。阿姐……她真的在这里?
以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形式?恐慌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愤怒攫住了我。我不再试图挣脱,
而是猛地伸出另一只自由的手,不顾一切地探向轿内,
想要抓住那枚尾戒——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那冰凉的银圈时,攥住我衣角的纸手,
猛地一扯!力量巨大无比,我整个人被带得一个趔趄,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去,
额头险些撞上轿门。与此同时,那纸人新娘一直固定不动的头颅,
发出极其轻微的“咔嚓”声,像是内部竹篾断裂的声响,猛地向我这边的角度,
又偏转了一些。它“看”着我,近在咫尺。那双描画的、没有瞳孔的眼睛,黑洞洞的,
仿佛两个深不见底的漩涡,要将我的魂魄都吸进去。它脸上那固定的笑容,
在如此近的距离下,放大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喜婆的声音再次响起,贴得极近,
带着河水的腥气吹进我的耳朵:“她等不及了……你得替她,先把这路……走完。”走完?
走去哪里?我的目光越过近在咫尺的纸人,
投向它身后那顶幽暗的、仿佛巨兽口腔的花轿内部。那里面,似乎比看上去要深得多,
黑暗浓稠得化不开,隐隐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散发出和陈旧纸张、腐败河水截然不同的、更古老、更令人不安的气息。
纸手的力量还在加大,要将我拖进那轿中去。喜婆搭在我手腕上的冰冷手指,
也开始施加压力。我像被两股力量夹在中间,动弹不得。而周围,那些沉默的镇民,
不知何时,已经围拢了上来,形成一个半圆,堵住了我所有可能的退路。他们依旧面无表情,
眼神空洞,像一群被无形丝线操控的傀儡,静静地注视着这场献祭。长明灯惨白的光,
跳跃着,在他们脸上投下明明灭灭、扭曲变形的影子。河水在身后,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发出空洞而持续的哗哗声,像是在催促。3 深渊之眼我的衣角,
被那只来自冥婚花轿的纸手,死死攥住,指向那深不见底的轿内黑暗。那黑暗里,
有什么东西,正在等待着。那纸手的力道大得异乎寻常,不似纸张,倒像冰冷的铁钳。
我被它拽得踉跄向前,膝盖重重磕在坚硬的轿槛上,钻心的疼。
喜婆那只枯手仍箍着我的手腕,寒意刺骨,像一条冻僵的蛇。视线被迫投进轿内。
刚才惊鸿一瞥的幽深,此刻扑面而来。轿子内部的空间在昏暗的光线下扭曲、扩张,
仿佛不再是一个实体的容器,而是一口通往地底深处的井。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在其中翻滚,
先前闻到的甜腻腐朽的香火味,在这里源头找到了,浓郁得让人作呕,几乎凝成实质,
堵塞着我的喉咙。而在那片翻滚的黑暗最深处,有东西在动。不是明确的形状,
更像是一团凝聚的阴影,比周围的黑暗更加深邃。它缓缓地、粘稠地蠕动着,
像某种沉睡的庞大生物无意识的呼吸。一股难以言喻的、混合着极端古老和彻底死寂的气息,
从那里弥漫出来,压得我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阿姐的尾戒,就掉落在轿门内侧边缘,
一半隐在黑暗里,闪着微弱的、求救似的银光。“阿…姐……”我喉咙像是被砂纸磨过,
挤出破碎的气音。就在我吐出这两个字的瞬间,那攥着我衣角的纸手,
猛地传来一股更狂暴的力量!同时,我清晰地感觉到,那粗糙的、糊着纸的手指,
似乎……嵌得更深了。不是拉扯,而是某种渗透。衣角被抓握的地方,
布料传来细微的、令人头皮发麻的撕裂声,而一种冰冷的、麻木的感觉,
正顺着被抓住的那一点,向我的皮肤下蔓延。喜婆的脸凑得更近,
她浑浊的眼珠里映不出任何光,只有我惊恐扭曲的倒影。“路,
总要有人走……”她呼出的气息带着河底淤泥的腥臭,“她回不来了……但你,
可以替她把债还上……”债?什么债?三十年的债?恐慌如同冰水浇头,
但求生的本能猛地炸开。我不能进去!进去就真的完了!
我另一只自由的手疯狂地在身边摸索,
指尖猛地触碰到腰间挂着的、原本用来防身的强光手电——阿姐失踪后我随时带在身上的。
金属的冰冷触感让我心神稍定。几乎是凭着肌肉记忆,我拇指用力按下开关!“咔哒。
”一道炽白的光柱,如同利剑,骤然劈开了轿前浓稠的昏暗,直直刺入那花轿内部的深渊!
光芒所至,那翻滚的黑暗像是活物般剧烈地扭曲、退缩了一下。也就在这一刹那,
我看清了——那蠕动的黑暗深处,根本不是什么阴影。是头发。
无数湿漉漉、纠缠在一起、沾满暗绿色水藻和淤泥的黑色长发,
像某种巨大的、不祥的水生巢穴,填满了轿厢后部的大部分空间。而在那团蠕动的发丝间隙,
隐约可见惨白的、浮肿的肢体轮廓,不止一具!它们像是被随意丢弃的破烂玩偶,
拥挤、折叠在那狭小的空间里,随着发丝的蠕动而微微起伏。最靠近轿口的那具“身体”,
面朝下,穿着一件褪色的、我依稀记得阿姐失踪那天穿着的鹅黄色衬衫的残片,
那颜色几乎被污渍浸染得看不出原貌。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扑鼻的恶臭让我胃里翻江倒海。
而光芒也照亮了攥住我衣角的那只纸手。它在强光下显得更加诡异,纸张的纹理粗糙,
竹篾的骨架清晰可见。但更可怕的是,我衣角被抓握的地方,
周围的布料颜色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暗、腐朽,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生机,
而那冰冷的麻木感,正顺着布料向我的腰部皮肤侵蚀!“呃啊——!”我发出不成调的嘶吼,
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我不再试图挣脱,而是将全身的重量向后猛坠,
同时握着电筒的手调转方向,用坚硬的金属尾部,狠狠砸向那只纸手的手腕连接处!“噗嗤!
”一声闷响,不像砸中纸张,更像砸进了潮湿的、充满败絮的泥土。
纸手的手腕处猛地凹陷下去,但没有断裂。反而,
一股暗红色的、带着浓烈铁锈和腥臭味的粘稠液体,从破损的纸张和竹篾缝隙里渗了出来,
滴滴答答,落在我的裤腿上和河滩的石子上。那液体触手冰凉粘腻。抓住我衣角的力量,
因为这猛烈的一击,骤然松懈了一瞬!就是现在!我腰腹猛地用力,配合着向后拼死一挣!
“刺啦——!”布帛撕裂的声响尖锐刺耳。一大片T恤下摆被硬生生扯断,
留在了那只依旧维持抓握姿势的纸手中。惯性让我向后猛退了好几步,
脚下被湿滑的石头一绊,重重摔坐在冰冷的河滩上,泥水瞬间浸透了裤子。
强光手电脱手飞出,“啪”地一声掉在几步外,光柱兀自亮着,
斜斜地照射着那顶静止不动的血红花轿,
以及轿口那只兀自抓着一块碎布、缓缓渗着暗红液体的纸手。轿帘,
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缓缓地、无声地垂落下来,隔绝了内里那令人作呕的景象。
喜婆站在原地,脸上那诡异的假笑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近乎怨毒的凝视。
她看了看轿子,又看了看跌坐在地、惊魂未定的我,干瘪的嘴唇蠕动了一下,
最终什么也没说。周围的镇民依旧沉默着,像一群失去指令的木偶。河水哗哗,
仿佛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切从未发生。但我手里,紧紧攥着那枚在最后关头,
我扑向前试图抓取尾戒时,指尖意外勾到的东西——它不是尾戒,
而是一个小小的、坚硬的、从轿内黑暗边缘擦过的物体。我颤抖地摊开手心。
那是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造型古怪的木质符牌,边缘粗糙,刻着无法辨认的扭曲纹路,
表面被摩挲得油亮,却透着一股阴邪的气息。它不属于阿姐。而我的衣角,
残留着被撕裂的破口,以及一股若有若无、萦绕不散的……来自那暗红液体的腥臭。
河新娘的仪式,似乎因为我这个意外而中断了。但我知道,没完。它,或者它们,盯上我了。
那轿子里的黑暗,和黑暗中蠕动的长发与肢体,以及喜婆那句“替她把债还上”,
像冰冷的毒蛇,缠上了我的心脏。阿姐的失踪,绝不仅仅是成为“替身”那么简单。
这沉默的小镇,这条吞人的河,藏着远比我想象中更黑暗、更古老的东西。
而我手里这枚陌生的符牌,或许是唯一的线索。
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从冰冷的河滩泥水里爬起来,顾不上满身的污秽和膝盖传来的钝痛,
一把抓起掉在地上的强光手电,光束慌乱地扫过那顶静止的血红轿子,
扫过沉默如鬼魅的送亲队伍,
最后落在我空空如也的身后——那片被黑暗和河水呜咽声填满的空旷河滩。没有脚步声,
没有阻拦。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一张张在惨白灯光下青灰麻木的脸,一双双空洞的眼睛,
无声地注视着我,像在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默剧。喜婆脸上那怨毒的凝视也消失了,
恢复成一种近乎石雕的漠然。这种沉默比追杀更让人胆寒。
4 逃离鬼镇我不敢再多停留一秒钟,攥紧手里那枚阴邪的木质符牌,
转身跌跌撞撞地朝着镇子的方向狂奔。湿透的裤腿黏在皮肤上,冰冷沉重,
每一次迈步都异常艰难。背后的河水声、风声,还有那死寂的送亲队伍,都像无形的针,
扎在我的脊梁骨上。跑!离开河边!离开这群疯子!肺叶火辣辣地疼,喉咙里全是血腥气。
直到冲进镇口那歪歪扭扭的牌坊,踏上粗糙的石板路,
看到零星几扇窗户里透出的、微弱得可怜的煤油灯光,我才敢稍微放缓脚步,
扶着旁边一堵长满青苔的湿滑墙壁,大口喘息。心脏还在疯狂地跳动,几乎要撞碎胸骨。
我摊开手心,那枚小小的木质符牌静静躺着。离开河滩后,它摸起来更加冰凉,
那股阴邪的气息似乎也淡了些,但指尖触碰时,
依然能感到一种细微的、令人不舒服的蠕动感,像是里面封着什么活物。这不是阿姐的东西。
它来自那顶花轿,来自那片蠕动着湿发和尸体的黑暗。这是线索,是揭开这恐怖谜团的关键。
镇上静得出奇,连狗吠声都没有。这个时间,本该是炊烟袅袅,结束一天劳作的时候,
可现在,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偶尔有窗帘缝隙后,似乎有眼睛在窥视,
但当我警惕地望过去时,那缝隙又立刻合拢了。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河边会发生什么!
一种孤立无援的绝望感漫上来。我现在该去哪里?回那间临河的老屋?
想到深夜可能再次响起的、湿漉漉的歌声,我就一阵头皮发麻。得找人问问。这符牌,
总该有人认得。我抹了把脸上的冷汗和泥水,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走向记忆中镇口那家兼卖杂货和草药的小铺子。
那是镇上为数不多还会对外来人稍显客气的地方。铺子门虚掩着,里面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
我推门进去,门轴发出“吱呀”一声怪响。柜台后坐着的是铺主老陈,
一个干瘦沉默的中年人。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
但很快又低下头,假装整理着柜台里那些蒙尘的货品。“陈叔,”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
将握着符牌的手伸到柜台上方,摊开,“您……认得这个吗?”油灯的光线跳跃着,
落在符牌扭曲的纹路上。老陈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他抬起头,目光快速扫过符牌,
又迅速移开,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更加蜡黄。他嘴唇哆嗦着,半晌,
才挤出一句:“不……不认得。你从哪儿弄来的?快……快扔了!”他的反应太过激烈,
反而证实了我的猜测。“河边,”我紧紧盯着他,“从那顶娶亲的花轿里。
”老陈猛地倒吸一口冷气,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向后缩去,
撞倒了柜台角落一个空着的竹篓。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不是对我,而是对我手心里的东西。
“拿走!快拿走!这东西沾不得!沾不得啊!”他声音发颤,几乎是在哀求,
“会……会招来不干净的东西!你快走!别连累我!”他一边说,一边慌乱地挥手,
像是要驱赶什么无形的厄运。我还想再问,但老陈已经彻底缩到了柜台最里面的阴影里,
背对着我,身体微微发抖,无论我再说什么,他都一言不发。线索断了。或者说,
恐惧堵住了唯一的缺口。我捏紧符牌,默默退出杂货铺。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浓重的夜色像墨一样泼洒下来,吞噬着小镇狭窄的街道和破旧的房屋。只有零星的灯火,
在黑暗中如同鬼火般飘摇。走在回老屋的路上,每一步都踩在悬空的恐惧上。风吹过屋檐,
带起呜呜的声响,像是无数冤魂在窃窃私语。阴影里,仿佛随时会伸出一只惨白的纸手,
或者晃过一团湿漉漉的头发。老屋的门依旧是我离开时虚掩的样子。我推开门,
一股比之前更浓重的霉味和灰尘气息扑面而来,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熟悉的河水腥气。
手电光柱在屋内扫过,客厅空荡,桌椅落满灰尘,阿姐的画板还支在角落,
上面蒙着一块白布。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但我浑身的汗毛却瞬间立了起来。不对。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没有歌声。但是,
空气里多了一种极其微弱的、湿漉漉的……摩擦声。很轻,很慢,
像是沾水的绸缎在地上拖行。声音的来源……是阿姐的卧室。我握紧手电,
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一步步挪向那扇紧闭的房门。摩擦声似乎停顿了一下。鼓足勇气,
我猛地推开房门!手电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床铺整齐,书桌依旧,窗户关着。
什么都没有。那摩擦声也消失了。是错觉吗?过度紧张产生的幻听?我喘着气,靠在门框上,
冷汗浸湿了后背。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靠窗的书桌桌面。桌子上,
原本盖在阿姐常用的那个速写本上的防尘布,被掀开了一角。而速写本,是摊开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离开前,防尘布是好好盖着的,速写本也是合拢的。有人进来过?
或者……有什么东西……我走到书桌前,手电光落在摊开的速写本页面上。那一页,
用炭笔画着的,不再是阿姐平时喜欢的风景或者人物素描。纸上,用一种狂乱而颤抖的笔触,
画着一顶极其精细、却又无比诡异的花轿。轿帘掀开一角,
里面伸出一只……没有皮肤、只有筋肉和惨白骨骼的手,死死地攥着一块衣角。
而在花轿旁边的空白处,用同样颤抖的笔迹,反复写着一行小字,密密麻麻,
几乎填满了所有空隙:“祂要的不是替身……是容器……”字迹的颜色,是暗红色的,
带着一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铁锈腥气。和我裤腿上,那纸手渗出的液体,一模一样。
那暗红色的字迹,带着铁锈与腥臭,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视网膜上。
“祂要的不是替身……是容器……”容器?什么容器?容纳什么?阿姐知道!
她失踪前一定发现了什么,并且用这种诡异的方式留下了信息!
这字迹的颜色……和那纸手渗出的粘稠液体一模一样!这不是普通的颜料,
这是……那东西的血?或者说,是某种更具污染性的存在?速写本上,
那顶被狂乱线条勾勒出的花轿,那支从轿中伸出的、筋肉裸露的骨手,仿佛要挣脱纸面,
再次攥住我。我猛地合上速写本,心脏在空荡的胸腔里疯狂擂动。屋外的风声似乎变了调,
夹杂着细碎的、湿漉漉的拖沓声,时远时近,缠绕着这栋孤零零的老屋。这里不能待了。
它们知道我来过,动过这东西。它们可能就在外面,或者在……这屋子的某个角落。
我抓起速写本,塞进随身的背包,连同那枚阴冷的木质符牌。强光手电的光柱因为电池消耗,
已经黯淡了不少,扫过房间角落的阴影时,那些影子仿佛活了过来,蠕动着,膨胀着。
必须离开!立刻!5 地底惊变我冲出老屋,一头扎进小镇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
冰冷的空气吸入肺腑,稍微驱散了一些屋内的窒闷腐臭。石板路湿滑,
两旁紧闭的门窗像无数只沉默的眼睛,窥视着我在黑暗中的狼狈奔逃。去哪里?镇公所?
那里或许有档案,有记录。这个小镇存在了不止三十年,河新娘的传说,这种诡异的仪式,
绝不可能毫无痕迹。还有那“容器”,到底是什么?镇公所是一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
孤零零地立在镇子中心的小广场边上,比周围的民居更加破败。木门上了锁,
一把老旧的铁锁,锈迹斑斑。我绕到楼后,找到一扇气窗,玻璃早已碎裂,
只用木板胡乱钉着。用力踹开松动的木板,一股陈年灰尘和纸张霉烂的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是档案室。手电光柱在弥漫的灰尘中划出苍白的光路,照亮一排排蒙尘的木架,
上面堆满了泛黄卷曲的纸页和线装册子。空气凝滞,带着故纸堆特有的死寂。
我从最近的架子开始翻找。大多是些田亩登记、户籍变动、物资调配的记录,枯燥乏味。
灰尘呛得我连连咳嗽,指尖拂过那些脆弱的纸页,仿佛在触摸时间的尸骸。没有。关于河流,
关于祭祀,关于任何超常事件的记录,一片空白。难道猜错了?
这些东西根本不会被记录在案?我不甘心,继续向档案室深处摸索。
角落有一个更加破旧的木箱,没有上锁,里面散乱地堆着一些更早期的、字迹模糊的册子。
我拿起一本封面破损、用繁体字写着《清河镇风土志略》的册子,随手翻动。
大部分内容依旧是无关紧要的记述。直到我翻到接近末尾的某一页。那一页的边缘,
被人用毛笔,小心翼翼地写下了一行娟秀的小字,墨色与印刷体截然不同:“水通幽冥,
非祀不宁。然以生魂饲之,其患愈深。林氏女秀珠,庚申年祭,异变始生。”字迹工整,
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惊惧。林秀珠?庚申年?那是哪一年?我快速心算,一个甲子六十年,
最近的庚申年是1980年,再往前是1920年……无论哪个,都远超三十年!异变始生?
什么意思?难道河新娘的祭祀,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并且因为一个叫林秀珠的女子,
发生了某种“异变”?而“以生魂饲之,其患愈深”,恰恰印证了阿姐留下的“不是替身”!
我继续疯狂翻找,手指被粗糙的纸边划破也浑然不觉。在另一本残破的账本夹缝里,
又找到了一行类似的批注:“彼之欲壑,非魂可填。需灵肉交融之器,方可承载其‘念’。
”灵肉交融之器……容器!批注的笔迹,和《风土志略》上的是同一个人!这个人,
似乎是在试图警告,或者记录下被官方掩盖的真相!我顺着堆放这个箱子的架子向上摸,
在最高一层,指尖触碰到一个用油布包裹的、硬硬的东西。取下来,打开油布。
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木质的神主牌位!做工粗糙,木质发黑,上面没有名字,
只用朱砂画着一个扭曲的、与我手中符牌纹路有几分相似的符号!而在牌位背面,
刻着两个几乎被磨平的小字:“秀珠”!林秀珠?!她的牌位为什么会在这里?被藏起来?
镇畏?还是……镇压?就在我手指触碰牌位背面那两个字的时候,
一股极其阴寒的气息顺着手臂猛地窜上来,同时,背包里的那枚木质符牌,突然变得滚烫!
“嗡——”一声低沉的、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震鸣,穿透档案室的墙壁和地板,
直接作用在我的骨骼上。几乎在同时,外面广场上,传来了声音。不是风声,不是水声。
是很多人的脚步声。僵硬,整齐,拖沓。慢慢地,由远及近,朝着镇公所的方向汇聚过来。
手电的光柱颤抖着移向窗外。黯淡的月光下,影影绰绰,
一个个人影正从四面八方的巷道里走出,沉默地聚集在广场上。他们穿着暗色的衣服,
低着头,看不清脸。和河边送亲的队伍,一模一样。他们被惊动了。因为我找到了这个牌位?
还是因为符牌的异动?脚步声在楼下停住。死寂。然后,是钥匙插入锁孔,
转动门锁的——“咔哒。”声。门,要被打开了。“咔哒。
”门锁转动的声音在死寂的档案室里异常清晰,像一颗冰锥扎进我的耳膜。
楼下的脚步声已经停了,他们就在外面,沉默地聚集着,等待着。那扇薄薄的木门,
根本挡不住什么。心脏骤停了一瞬,随即疯狂地泵送着冰冷的血液冲向四肢百骸。
不能从正门走!我猛地抓起桌上那块刻着“秀珠”的漆黑牌位,
连同那本写有批注的《风土志略》,一股脑塞进背包,与那枚滚烫的符牌挤在一起。
背包内部传来一种诡异的、低频率的震动,仿佛里面的东西正在相互呼应,
或者……相互排斥。手电光柱慌乱地扫向四周。来时的那扇气窗太高,
而且外面很可能也有人堵着。档案室深处,靠墙的位置,堆放着几个破旧的麻袋,
散发着陈年谷壳和尘土混合的气味。麻袋后面,似乎有一片更深的阴影。我几乎是扑了过去,
手脚并用地扒开那些散发着霉味的麻袋。灰尘呛得我眼泪直流。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