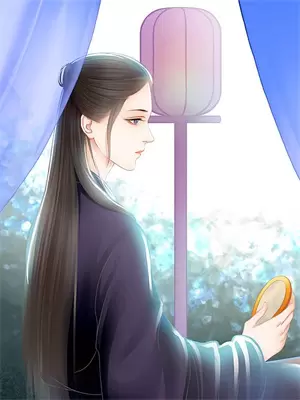暮春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黏腻,敲在青瓦上淅淅沥沥,把整座老宅泡得发涨。
沈清辞拎着行李箱站在雕花门楼前,铜环上的绿锈蹭在指尖,凉得像块冰。门是虚掩的,
推开来时发出悠长的“吱呀”声,惊起梁上几只灰雀,扑棱棱掠过天井,
翅膀带起的雨珠落在青石板上,洇出星星点点的湿痕。她是第一次来这座祖宅。
三天前接到律师函,说远房姑婆留了遗嘱,把这座位于城郊的沈家老宅留给了她。父亲早逝,
母亲提起沈家时总带着种讳莫如深的疏离,只说那宅子“阴气重”,让她别沾。
可眼下母亲重病住院,催款单像雪片似的飞来,这座荒废了二十多年的老宅,
成了唯一的指望。客厅里结着厚厚的蛛网,阳光被雕花窗棂切碎,落在积灰的八仙桌上,
照出无数浮动的尘埃。墙角摆着座褪了色的梨花木梳妆台,镜面蒙着层白雾,
隐约能映出人影。沈清辞放下行李箱,指尖刚碰到梳妆台的抽屉,就听见二楼传来轻响,
像是有人踩着木地板走过,脚步很轻,带着种拖沓的滞涩。她猛地抬头,楼梯口的光线昏暗,
雕花栏杆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露出底下暗沉的木色。“有人吗?”她喊了一声,
声音撞在墙壁上,反弹回来时变得闷闷的,带着点回音。没有回应。只有雨声依旧,
敲在窗上,敲在心上,敲得人发慌。收拾到傍晚,雨总算小了些。
沈清辞在厨房找到个能用的铁锅,烧了壶热水,水汽氤氲中,
恍惚看见灶台边立着个模糊的影子,穿着件月白长衫,袖口绣着暗纹,正弯腰往灶膛里添柴。
她惊得手一抖,水壶“哐当”撞在锅沿上,影子倏地散了,只剩灶膛里跳动的火苗,
映得墙壁上的裂纹忽明忽暗。夜里躺在客房的雕花木床上,被褥带着股陈旧的樟脑味。
窗外的芭蕉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有人在窗外窃窃私语。沈清辞翻了个身,
忽见帐顶垂下一缕黑发,发丝很软,扫过她的脸颊,带着点冷香,像是某种不知名的花香,
又混着点潮湿的泥土气。她屏住呼吸,猛地拽开帐子,什么都没有。只有月光从窗棂漏进来,
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其中一块影子微微晃动,像是被人踩了一脚。接下来的几天,
怪事接连不断。她放在桌上的梳子会莫名出现在梳妆台上,
晾在院子里的衣物总被人拧成奇怪的结,夜里总能听见二楼传来断断续续的琴声,调子哀婉,
像是民国时的老曲子。沈清辞不是没想过离开,可母亲的医药费像座大山压着,
她只能硬着头皮联系中介,商量出售老宅的事。中介来看房那天,刚走到楼梯口就摔了一跤,
脚踝肿得像馒头,嘴里嘟囔着“邪门”,再也不肯踏进来半步。这天傍晚,
她在书房整理姑婆留下的旧物,翻到本泛黄的线装书,书页间夹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旗袍的女子,眉眼温婉,站在天井的石榴树下,怀里抱着只白猫。
女子身边站着个年轻男子,正是她傍晚在厨房看见的那个身影,月白长衫,眉目清俊,
正低头看着女子,眼里的温柔几乎要溢出来。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行小字:“民国二十六年,
赠砚之,清沅。”沈清辞的心猛地一跳。清沅,是姑婆的名字。那这个叫砚之的男子是谁?
她把照片夹回书里,刚要合上,却见书页边缘有行娟秀的批注:“今夜雨急,君归否?
”墨迹晕开了些,像是被泪水浸过。夜里琴声又响了,比往常更清晰,像是就在隔壁房间。
沈清辞披衣下床,循着声音走到二楼最东头的房间。门是锁着的,她从发间取下根发卡,
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摆弄锁孔,“咔哒”一声,锁开了。房间里积着厚厚的灰,
正中央摆着架老式钢琴,琴盖敞开着,琴键上蒙着层尘。可那琴声明明还在响,
从琴键上流淌出来,哀婉缠绵,正是她这几天总听见的调子。沈清辞走到钢琴前,
指尖悬在琴键上方,不敢落下。忽然,一阵冷风从窗外灌进来,吹得窗帘猎猎作响,
琴键自己动了起来,按下一串音符,正是那首曲子的收尾。她吓得后退半步,
撞在身后的书架上,几本旧书“哗啦”掉下来,砸在地板上。其中一本摊开着,
里面夹着的信纸飘落到脚边。信纸上的字迹和照片背面的一样,是姑婆的笔迹:“砚之,
他们说你投了敌,我不信。可这宅子里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父亲把我锁了起来,
说要让我嫁给张旅长……砚之,你来带我行吗?哪怕只是魂魄,我也等你。
”信纸的边缘有干涸的暗红印记,像是血迹。沈清辞捡起信纸,忽然觉得背后一凉,
像是有人在盯着她。她猛地回头,只见月光下,钢琴旁站着个模糊的身影,
正是照片上的那个男子,月白长衫在风中微动,面容却看不真切,只有一双眼睛,
温柔得让人心头发颤。“你是谁?”沈清辞的声音有些发颤,却并不害怕。男子没有回答,
只是抬手,指向书架顶层。沈清辞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摆着个小小的紫檀木盒。
她搬来椅子,取下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放着枚青玉印章,刻着“砚之”二字,
旁边还有半块撕碎的手帕,上面绣着朵残荷,和照片上女子旗袍上的花纹一模一样。
“民国二十七年,沈清沅于家中自缢。”一行小字刻在印章的侧面,字迹潦草,
像是刻得很急。沈清辞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姑婆是自缢的?那她等的人呢?
这个叫砚之的男子,最后来了吗?她抬头再看,钢琴旁的身影已经不见了。琴声也停了,
只有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像是谁在哭。接下来的日子,沈清辞不再想着卖房。
她开始整理老宅里的旧物,试图拼凑出那段被遗忘的往事。她在姑婆的日记里看到,
砚之原是位教书先生,和清沅相爱,却因沈家嫌弃他家境贫寒而被拆散。后来战乱起,
砚之被诬陷投敌,清沅不信,苦苦等他,却被家人逼迫,最终选择了绝路。日记的最后一页,
画着一幅小小的素描,是那架钢琴,旁边写着:“琴在,人等。”这天夜里,
沈清辞又听见了琴声,这次她没有害怕,而是走到钢琴旁,学着记忆里的调子,按下了琴键。
她弹得生涩,却断断续续地把整首曲子弹了下来。一曲终了,身后传来轻微的叹息。她回头,
看见砚之就站在那里,这次他的面容清晰了些,眉眼间带着化不开的悲伤。“她总说,
我弹的曲子里有雨的味道。”他的声音很轻,像风拂过水面。“你一直在这里?”沈清辞问。
“我回来过,”他望着窗外的雨,眼神悠远,“可她已经不在了。我找不到她,
只能守着这宅子,守着她的琴声。”沈清辞的心一酸:“她等了你很久。”“我知道,
”他抬手,像是想触碰什么,指尖却穿过了她的发梢,“我被人陷害,在牢里待了三年,
出来时,沈家已经败落,她……也不在了。我在这宅子里等了七十多年,总想着,
或许她的魂魄还在,能听见我的琴声。”月光透过窗棂,照在他身上,
他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谢谢你,”他看着沈清辞,眼里带着感激,“让我知道,
她一直信我。”“她的日记里,每一页都在等你。”沈清辞说。他笑了,那笑容里带着释然,
也带着无尽的怅惘。“雨停了,我该走了。”他的身影越来越淡,像水墨晕开在宣纸上,
“这宅子,留给你了。还有……”他顿了顿,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替我告诉她,
我从未负她。”身影消失了,琴声再也没有响起过。沈清辞把老宅重新修缮了一番,
没有卖掉。母亲的病渐渐好转,偶尔会来老宅小住。某个午后,母亲坐在天井里晒太阳,
看着那架钢琴,忽然说:“小时候听你外婆说,你姑婆年轻的时候,总爱在雨天弹琴,
说有个穿白衣服的公子会来听。当时只当是瞎话,现在看来……”沈清辞没有说话,
只是拿起那枚青玉印章,阳光下,玉色温润,仿佛还带着那个人的体温。她走到钢琴旁,
打开琴盖,忽然发现琴键下压着张小小的便签,是她从未见过的字迹,
和印章上的“砚之”二字如出一辙:“清沅,雨停了,我来接你了。”便签的边缘,
沾着一点淡淡的、不知名的花香,像极了那天夜里,拂过脸颊的冷香。
窗外的石榴树抽出了新芽,绿意盎然,仿佛在诉说着一个跨越了漫长岁月的、未完的故事。
梅雨季节的雨总带着股挥之不去的缠绵,修缮老宅的工匠们撤场后,
沈清辞独自坐在天井的石凳上,看着檐角滴落的水珠在青石板上砸出浅浅的坑洼。
石榴树的新叶被雨水洗得发亮,叶尖垂着的水珠折射出细碎的光,
落在那架老式钢琴的琴盖上,像撒了把碎银。她伸手抚过琴盖边缘的雕花,木质温润,
带着被岁月打磨过的光滑。自砚之的身影消失后,这架琴再没自动响起过,可沈清辞总觉得,
琴箱里还藏着些什么,像浸在雨里的秘密,沉甸甸的,不肯浮上来。这天傍晚,
她整理姑婆的梳妆台,在最底层的抽屉里摸到个硬纸筒,筒口用红绳系着,绳结已经发脆,
一扯就断了。倒出来的是几卷泛黄的画纸,墨迹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了些,
画的都是同一个场景——老宅的天井,石榴树下站着个穿旗袍的女子,手里抱着本书,
有时抬头望着二楼的窗,有时低头看着地面,裙摆上总沾着点石榴花的红。
最后一卷画纸里夹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宣纸,上面是幅未完成的素描,画的是砚之,
他坐在钢琴前,侧脸的线条清俊,手指悬在琴键上方,眼神里带着种沈清辞从未见过的温柔。
画的右下角有行小字:“民国二十六年五月,雨,他说琴键是有温度的。
”沈清辞的指尖拂过那行字,宣纸的纤维带着点涩感,像是能摸到当时落笔的轻颤。
她把画纸重新卷好,放回纸筒时,指尖触到筒底有个硬物,倒出来一看,是枚银质的书签,
镂空的花纹已经发黑,上面刻着个“沅”字。书签的背面粘着张极小的纸片,
像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两个字:“西廊”。西廊是老宅西侧的一排耳房,
常年漏雨,修缮时工匠说木料已经朽了,建议拆掉,沈清辞没舍得,
只让他们做了简单的加固。此刻她捏着那枚书签,心里像被雨泡过的棉絮,沉甸甸的。
西廊……那里藏着什么?夜雨又起时,沈清辞提着盏煤油灯走进西廊。
廊下的地面积着层薄灰,脚印杂乱,是工匠们留下的。廊尽头的房间挂着幅褪色的蓝布帘,
布帘边角已经霉烂,被风一吹,露出里面黑黢黢的角落。她掀开布帘,煤油灯的光忽明忽暗,
照亮了堆在墙角的旧物——几口蒙着布的木箱,一把断了弦的胡琴,还有个落满灰尘的鸟笼,
笼门开着,里面空空如也。沈清辞的目光落在最左边的木箱上,
箱盖缝隙里露出点暗红的布角,像是旗袍的料子。她蹲下身,吹掉箱盖上的灰,
铜锁已经锈死,只能用石块砸开。箱盖“吱呀”一声弹开,
一股混合着樟脑和霉味的气息涌出来,呛得她后退半步。箱子里叠着几件旗袍,
颜色都已暗淡,领口的盘扣却还亮着,其中一件月白色的旗袍下摆处,沾着块深色的污渍,
像是干涸的血迹,边缘还留着撕扯的痕迹。旗袍下面压着本厚厚的相册,
封面是暗红色的绒布,烫金的“纪念”二字已经磨得只剩轮廓。翻开第一页,
是沈清沅和砚之的合影,两人站在西廊的廊下,砚之手里拿着本书,清沅靠在他身边,
笑得眉眼弯弯,照片的边缘有处折痕,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往后翻,大多是清沅的单人照,
有时在书房写字,有时在花园浇花,直到某一页,照片突然变成了空白,
只剩下贴照片的胶痕,形状是两个人的轮廓。再往后,是几张报纸的剪报,标题都模糊了,
只能看清“通敌叛国”“沈家公子”等字眼,旁边用红笔圈着个名字——顾砚之。
沈清辞的心猛地一沉。顾砚之……原来他姓顾。她想起清沅日记里的话,
“他们说你投了敌”,原来那些流言不是空穴来风。可照片里他望着清沅的眼神,
那样干净温柔,怎么会是叛国之人?相册的最后一页夹着张药方,字迹潦草,
像是急着写就的,上面只有几味药:“当归三钱,苏木五钱,
红花……”都是些活血化瘀的药材,药方的右下角写着个日期,正是清沅自缢的前三天。
她把药方捏在手里,纸边发脆,一捏就掉渣。清沅当时是受伤了吗?
还是……这药方根本不是给她自己的?煤油灯的油快烧尽了,火苗越来越小,
映得墙上的影子忽大忽小,像有人在背后晃动。沈清辞站起身,刚要转身,
却瞥见鸟笼旁边的墙角,有块地砖比周围的颜色浅些,边缘还留着撬动的痕迹。她蹲下去,
用手指抠住砖缝,猛地一掀,地砖被掀开了,下面是个黑漆漆的洞,洞里放着个小小的陶罐。
陶罐上盖着块布,揭开布,里面装着些零散的铜钱,还有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油纸已经发黄,层层揭开,里面是半封信,信纸被水浸过,字迹模糊不清,
只能辨认出几句:“……狱中遇袭,恐难生还……清沅吾爱,勿等……沈家非良地,
速离……”落款处的名字被血渍糊住了,只剩下个“顾”字。沈清辞的指尖抖得厉害,
半封信像块烙铁,烫得她手心发疼。顾砚之在牢里遇袭了?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所以才让清沅离开?可清沅没有走,她选择了留在这座老宅里,
用死亡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她把半封信放回陶罐,刚要盖地砖,
却发现洞底还粘着张极小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个地址:“城郊乱葬岗,
第三棵歪脖子树下。”乱葬岗……沈清辞的心跳漏了一拍。那地方她小时候听母亲说过,
是民国战乱时扔死人的地方,早就荒了,据说晚上还有鬼火。顾砚之的信里说自己恐难生还,
难道……他的尸骨就在那里?夜雨下得更急了,西廊的窗户被风吹得“哐当”作响,
像是有人在外面拍打着玻璃。沈清辞把地砖盖好,用脚踩实,转身往外走时,
衣角却被什么东西勾住了。她低头一看,是鸟笼的铁丝,不知何时缠上了她的裙摆,
铁丝上锈迹斑斑,刮得布面起了毛。她解开铁丝,刚要迈步,却听见身后传来极轻的叹息,
像是从陶罐里钻出来的,带着点潮湿的土腥味。沈清辞猛地回头,煤油灯的光刚好耗尽,
西廊瞬间陷入一片漆黑,只有窗外的闪电偶尔划破黑暗,照亮墙角那几口沉默的木箱,
像几具蹲伏的影子。回到客房时,沈清辞浑身都湿透了,冷得发抖。
她把半封信和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雨,心里像压着块石头。
去还是不去?如果顾砚之的尸骨真在乱葬岗,她该把他迁回来吗?迁回来,又该葬在哪里?
和清沅的衣冠冢并排,还是……天亮时雨停了,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桌上,
那半封信上的血渍在光下泛着暗褐色的光。沈清辞咬了咬牙,找了把铁锹,
揣着纸条往城郊走去。乱葬岗比她想象的更荒凉,杂草长得比人还高,断碑残垣散落在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