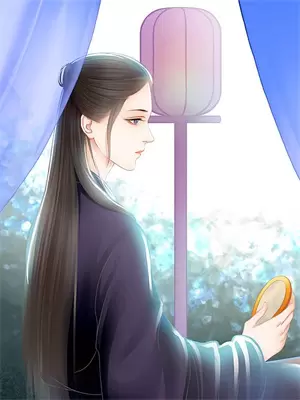父亲的尸体浮在河面上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最先发现的是清晨去河边洗衣的刘婶。
她后来逢人便说,那天河面雾气缭绕,父亲就那样直挺挺地漂在水面上,面朝天空,
眼睛瞪得像铜铃,仿佛死前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更诡异的是,他全身泡得发白肿胀,
唯独那双眼睛,清澈的吓人,黑白分明,宛如活人。那是死不瞑目啊。
村里的老人私下里摇头,怨气太重,怕是走得不甘心。我接到消息从城里赶回村里时,
父亲已经躺在祠堂的木板上,盖着白布。村支书和几个长辈围在一旁,面色凝重。
他们众口一词,说父亲是在河边散步时失足落水,纯属意外。可我知道不是。
父亲一辈子怕水,自从十年前母亲在那条河里淹死后,父亲连河边百米内都不愿靠近。
这样一个对水畏之如虎的人,怎么会半夜独自去河边?爸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我问姐姐。
姐姐眼神闪烁,不敢直视他:没、没什么异常。可能就是心里闷,去散步吧。
这解释站不住脚。我记得最后一次和父亲通电话,是在他死前三天。父亲声音洪亮,
笑着说等秋收了就去城里看我,还说要带自己腌的咸菜。我掀开白布,
父亲的面容已经过整理,但依然看得出水浸的痕迹。
最令人不安的是那双眼睛——尽管已经合上,但我总觉得它们还在注视着什么。当天晚上,
我梦见父亲站在河边,浑身湿透,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只有那双眼睛,
死死盯着我,充满了未尽的嘱托和警告。醒来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清父亲死亡的真相。
父亲下葬那天,天色阴沉得像一块浸透了污水的脏抹布,低低压在每个人头顶,
连风都带着一股土腥和腐朽的混合气味,沉甸甸得让人喘不过气。
村民们稀疏地站在新挖的坟坑四周,不像送葬,倒像是围观什么不祥之物。我站在姐姐身边,
能清晰地感觉到她单薄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是哭泣的抽动,而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寒意,
让她牙关都在打颤。粗粝的麻绳摩擦着棺木,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父亲的棺材被缓缓吊起,
又沉沉放入那方潮湿的土坑。当第一铲带着碎石块的黄土,啪一声砸在暗沉的棺盖上时,
异变陡生。身边的姐姐猛地一僵,随即像是被一股无形的电流击中,开始剧烈地抽搐起来。
她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响,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仰倒,
四肢以一种违背生理结构的角度扭曲、弹动,关节处发出细微的咔哒声。她双眼翻白,
只剩下浑浊的眼白,嘴角涌出带着泡沫的涎水。癫痫!快按住她!有人失声喊道,
带着惊慌。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的血液都几乎冻结。原本瘫软在地的姐姐,
竟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她动作却迅捷得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直扑向坟坑。她十指如钩,
疯了一样刨挖着刚填下去的新土,干燥的黄土与潮湿的泥块在她的指甲下翻飞,
指尖瞬间血肉模糊。不要埋我!不要埋我!里面闷…好黑…好冷啊—!姐姐尖声嘶吼,
那声音完全变了调,嘶哑,破裂,带着一种溺水之人垂死挣扎的绝望和浸入骨髓的寒意,
在山坡上凄厉地回荡。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源自亡者的可怖控诉,
钉在了原地。李老汉那张布满沟壑的脸瞬间失了血色,他猛地推开身前的人,
嘶声喊道:快!按住她!几个原本愣着的壮汉如梦初醒,一拥而上。可此时的姐姐,
身体里仿佛注入了非人的力量,三四条汉子竟也按不住她。她四肢疯狂地挥舞、挣扎,
喉咙里持续发出那种溺水般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嗬嗬声,
泥土和草屑沾满了她扭曲的脸庞。一个壮汉差点被她甩开,
脸上还被她无意识抓出了一道血痕。李老汉眼中精光一闪,不再犹豫。他一个箭步上前,
瞅准时机,一记干净利落的手刀精准地劈在姐姐后颈。姐姐身体猛地一僵,
随即像断了线的木偶,软软地瘫倒在地上。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众人粗重的喘息声和压抑不住的惊惧抽气。扶她坐好,别让她沾地气。
李老汉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去个人,拿碗清水,再拿双竹筷来!快!
东西很快备齐。一只常见的青花大碗,盛着八分满的清澈井水,被端到依旧昏迷的姐姐面前。
李老汉接过那双普普通通的竹筷,神色凝重如山雨欲来。所有围观者,都屏住了呼吸,
眼睛死死盯住那只碗。李老汉站在姐姐身侧,双手握住筷子,使其并拢,
垂直地、缓缓地插入水中。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仪式感:是张生哥吗?是你有话未说吗?是的话,就让这筷子,
立起来!话音刚落,那双原本该漂浮或倾倒的竹筷,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托住,
在水中微微晃动了几下,然后,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
颤巍巍地、违背常理地——直立了起来!筷子稳稳地立在清水中,仿佛扎根了一般。
嘶——人群中爆发出整齐的倒吸冷气声。村民们脸上写满了恐惧,
齐刷刷地向后退了一大步,仿佛那碗里立着的不是筷子,而是父亲含怨的鬼魂。
李老汉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凑近那只碗,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安抚和承诺:张生哥,
看到了…我们知道了…你安心走吧,身后事有我们,定会查清楚你是咋没的,
不让你死得不明不白…莫要缠着孩子,她还是个娃娃,禁不住啊…仿佛听到了他的话语,
那直立在水中的筷子,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支撑,啪嗒一声,轻响却如惊雷,倒在了碗底,
溅起几星细小的水花。那股笼罩在坟地的无形寒意,仿佛也随之骤然消散。但恐惧的种子,
已深埋进每个围观者的心里。姐姐被抬回家后,便大病了一场。她高烧不退,整日昏睡,
偶尔惊醒便是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有时是凄厉的不要埋我!,
有时是破碎的哀求我错了…放过我…,更多时候,
则是含混不清的、仿佛与人争辩的呓语,听得我心惊肉跳。这场大病来势汹汹,
几乎耗尽了姐姐的精气神,整整半个月,她才勉强能够下床走动,
但眼神里总是蒙着一层惊魂未定的阴影,人也沉默消瘦了许多。而我,
在经历了葬礼上那惊悚一幕后,心中疑云不仅未散,反而更加浓重。父亲诡异的死状,
姐姐匪夷所思的中邪…这一切都像一根根绳索,勒得我喘不过气。我向公司续了长假,
决定留下来,非要把父亲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村里关于父亲死因的流言愈发甚嚣尘上。
老人们聚在村口老槐树下,言之凿凿地说,父亲准是被河里的水鬼拖下去做了替身。
那条河邪门得很呐,他们压低声音,仿佛怕被什么听见,每隔几年就要收一条人命,
不然河神会发怒的。十年前他婆娘,现在轮到他,这是命里注定……
我从来都不信什么水鬼河神,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我只相信证据和逻辑。
父亲怕水是刻在骨子里的,绝不会深夜无故靠近河边。那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迫使他去了那里,或者,是有人把他带去了那里。夜幕再次降临,村里灯火零星,万籁俱寂。
我揣着一把强光手电,独自一人来到了那条吞噬了父亲的河边。夜晚的河流与白天截然不同,
湍急的水流在黑暗中发出呜咽般的哗哗声,像是不息的低泣。河风带着湿冷的寒意,
钻进我的衣领。手电筒的光束切开浓稠的黑暗,照在浑浊湍急的水面上,
只反射出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光斑,仿佛水下有无数双眼睛在窥视。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父亲被发现的那片河滩徘徊,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寸泥地、每一簇草丛,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就在这里,父亲失去了生命。也就在这里,或许隐藏着他死亡的真相。
手电光无意间扫过一丛虬结的水草,一个不自然的、带着些许反光的物件,
突兀地闯入了我的视线,是父亲的手机,卡在石缝中,居然还没完全坏掉。回到家,
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机烘干,接上电源。奇迹般地它开机了。手机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直到我点开录音功能。里面有一段录音,日期是父亲死前那晚。我点开播放。先是一阵风声,
然后是父亲急促的喘息声。在河边……那孩子……我浑身冰冷。那段录音里的背景音中,
有一个微弱但熟悉的声音在叫爸爸。是姐姐的声音。我突然想起父亲死后姐姐的异常,
她总是避开与我对视,她的高烧中的呓语:不是我...不是我...
疑点像毒藤一样缠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我揣着那部浸过水、带着父亲最后信息的手机,
去了镇上。我找到一个精通手机维修的朋友,将手机递过去,
只嘱咐了一句:想办法恢复里面删除的数据,特别是出事那几天的。多少钱都行。
朋友看出我眼中的血丝和执拗,点了点头。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直到日头偏西,
才拿着尚未修复的手机,心事重重地往回赶。踏进村口时,天色已近黄昏。
李老汉从村口那棵老槐树的阴影里缓缓走了出来,拦在了路中间。他显然已在此等候多时,
嘴里叼着的旱烟袋一明一灭,映照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上那挥之不去的凝重。雨子,
李老汉吐出一口浓烟,声音沙哑,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回来了?
我心头一紧:李伯,您在这……等你。李老汉打断我,浑浊却锐利的眼睛直视着我,
听人说,你去镇上了?是为了你爹手机的事?我没有否认。李老汉深深叹了口气,
那叹息里仿佛承载着整个村庄的重量:娃啊,听我一句劝,别再查了。有些事,刨根问底,
对你没好处。真相…有时候比糊涂更伤人。这话如同点燃了引线,
连日来的压抑、悲伤、疑惑和那坟地惊魂留下的恐惧,让我瞬间爆发出来。我猛地向前一步,
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别再拿这些话搪塞我!李伯,你告诉我实话,
我爸根本就不是意外落水,对不对?他是被人害死的,是不是谋杀?!最后两个字,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在异常寂静的村落里显得格外刺耳。李老汉的瞳孔似乎微微收缩了一下,
他沉默地嘬着烟嘴,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晦暗不明。他没有承认,但那份沉重的沉默,
以及眼神里一闪而过的、近乎怜悯的复杂情绪,本身就像是一种无声的回答。
我揣着满腹的疑云和李老汉那意味深长的警告回到家中时,屋里飘散着久违的饭菜香气。
姐姐正在厨房里忙碌,她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确实比前些日子结实了不少,
脸上也恢复了些许血色,正专注地翻炒着锅里的菜。这幅寻常的景象,
暂时驱散了村口带来的寒意。我靠在厨房门框上,没有立刻提起村口的遭遇,
而是选择了一个看似不经意,实则在心里反复掂量过的问题。姐,你还记得二十年前,
河里淹死的那个小女孩吗?好像叫…小玲?哐当——!话音刚落,
姐姐手中的铁铲猛地脱手,重重砸在铁锅边缘,然后又跌落在水泥地上,
发出一串刺耳的声响。锅里原本滋滋作响的菜瞬间糊了边,焦味弥漫开来。
她整个人僵在原地,背对着我,肩膀线条骤然绷紧。过了好几秒,她才缓缓转过身,
脸上刚刚恢复的那点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嘴唇微微翕动,
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慌和一种…几乎是本能般的防御。为…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她的声音干涩、紧绷,像一根快要断裂的弦。我的心沉了下去,姐姐这过激的反应,
无疑印证了我的某些猜测。我向前走了一步,目光紧紧锁住姐姐,
不再掩饰自己的探究:这和他那晚去河边有关,对不对?姐姐猛地避开了我的视线,
像是被烫到一样。她几乎是仓促地弯下腰,手有些发抖地捡起地上的铲子,然后拧开水龙头,
一遍遍地、机械地冲洗着已经干净的铲头,水流哗哗作响。她始终用后背对着我,
仿佛那样就能隔绝我的问题。不记得了。她的声音从水声里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