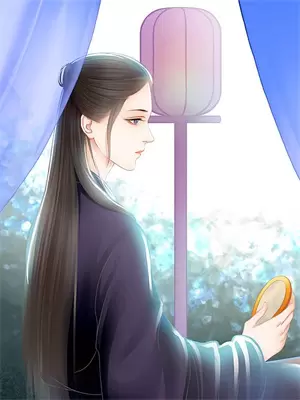在我们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拍合照时,绝对不能喊茄子。
新来的支教老师不信邪,毕业那天,他举起相机,让全班孩子笑着大喊:茄子!
照片洗出来后,他疯了。照片上,三十个孩子笑容灿烂,嘴巴却都诡异地咧到耳根,
像是被无形的手撕开。而他们的嘴里,没有舌头,塞满了黑紫色的、还在微微蠕动的茄子。
我默默收起那张合照,把它和我藏在床底的其他二十九张,整齐地叠在了一起。每一张,
都来自一届毕业的学生。1. 白衬衫的诅咒新来的支教老师叫陈宇,来我们落茄村
的那天,阳光很好。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
看起来和我们这个常年笼罩在灰蒙蒙雾气里的村子格格不入。村长领着他,挨家挨户地认人。
走到我家门口时,陈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温和地笑了笑:这位是?林晚,
我们村的会计,以后你的工资就找她领。村长浑浊的眼睛瞥了我一眼,语气没什么温度。
我点点头,没说话。陈宇似乎想拉近关系,主动伸出手:林会计你好,我叫陈宇,
以后请多指教。他的手掌宽厚温暖,和村里男人那些粗糙干裂的手完全不同。
我只飞快地握了一下就松开,指尖却像被烫到一般。村里已经很久没有外人来了。上一个,
还是三十年前。陈宇对村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对孩子们。
他很快就和那三十个即将毕业的孩子打成了一片,教他们念书、唱歌,
给他们讲山外的世界。孩子们很喜欢他,那一张张本该有些木然的小脸上,
渐渐有了鲜活的生气。我偶尔会去学校送些东西,隔着窗户,
能看到陈宇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样子。他讲到高兴处,会拿出手机,给孩子们看城市的照片,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对未知的渴望。我却只觉得心头发冷。
有一次,我去找村长汇报账目,正好听到他在和几个村里的老人说话。那个姓陈的,
太出格了。一个老人敲着烟杆,孩子们的心都让他说野了。村长坐在太师椅上,
闭着眼,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无妨。种子在土里待久了,总要见见光,才长得壮。
等毕业那天,一切就都回到正轨了。他的声音很平淡,却让我后背窜起一股凉意。
我抱着账本,悄无声地退了出去。那天晚上,我破例找到了正在备课的陈宇。陈老师。
我站在教室门口,昏黄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看到我有些意外,
连忙起身:林会计?这么晚了,有事吗?村里的孩子,从来不拍合照。我开门见山,
声音干涩。陈宇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为什么?是觉得照相机不吉利吗?这都是迷信。
不是迷信。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拍照可以,但千万,
千万不能喊『茄子』。他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愚昧的宽容:林会计,我知道你们村有很多老规矩。
但『茄-子』这个口型,能让笑容看起来最灿烂,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我不信的脸,所有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我怎么跟他解释?
说我们村之所以叫落茄村,是因为村子底下,埋着一个以茄子为食的神?
说村里的孩子,都是献给神的祭品,而毕业典礼,就是献祭的仪式?说那句茄子,
就是唤醒他们体内种子的咒语?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只能重复那句苍白的警告:信我一次,陈老师。为了孩子们,也为了你自己。说完,
我转身离开,没有再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不会信的。就像三十年前,
那个同样穿着白衬衫的支教老师一样。2. 茄子之咒毕业典礼那天,天气阴沉得可怕,
像是要塌下来。村长和老人们都穿上了黑色的对襟褂子,面无表情地坐在操场边上,
像一排排沉默的乌鸦。孩子们换上了新衣服,是陈宇自掏腰包给他们买的。他们站成一排,
脸上带着即将远行的兴奋和对陈宇的孺慕。陈宇站在他们面前,举着一台老式的胶片相机。
那是他特意从城里带来的,他说,要给孩子们一个最有仪式感的告别。孩子们,
我们来拍一张毕业照,好不好?他高声喊道。好!孩子们的声音清脆又响亮。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村长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身上,
那眼神像是在警告我安分一点。我低下头,攥紧了衣角。都准备好了吗?看着镜头!
陈宇调整着焦距,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大家一起,笑得开心一点!来,
跟我一起喊——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那个禁忌的词。茄——子——!
三十个孩子,用他们最纯真的笑脸,跟着他们最敬爱的老师,齐声高喊:茄——子——!
咔嚓。快门声响起,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操场上死一般的寂静。
陈宇还保持着拍照的姿势,脸上的笑容却慢慢凝固。他面前的孩子们,
依旧保持着微笑的表情,但那笑容却开始变得诡异。他们的嘴角不受控制地向上咧开,
一点点,一点点,越过正常的弧度,朝着耳根的方向撕裂。没有血。裂开的嘴里,
也不是鲜红的血肉和白色的牙齿。一截黑紫色的东西,从他们的喉咙深处,
缓缓地、缓缓地顶了出来。那东西表面光滑,带着黏液,还在微微地蠕动。是茄子。
是刚刚成型,还带着生命力的,茄子。三十个孩子,三十张被撕裂到耳根的笑脸,
三十张被蠕动的茄子塞满的嘴。他们就那样笑着,站着,
眼睛里还残留着对陈宇的信赖和喜爱。啊——!!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死寂。
陈宇扔掉相机,踉跄着后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惊恐地指着那些孩子,
眼珠子瞪得快要掉出眼眶,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像是被扼住了脖子。村长站起身,
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捡起了地上的相机。早就跟你说过了。他叹了口气,
语气里听不出是惋惜还是别的,为什么就是不信呢?几个村民走上前,
面无表情地架起已经语无伦次的陈宇,把他拖向村委会后面的祠堂。那是用来关押不听话
的外来者的地方。村长走到那排毕业的孩子面前,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好孩子们,
毕业了。他说,该去你们该去的地方了。孩子们像是提线的木偶,僵硬地转过身,
迈着整齐的步伐,朝着村后那片广袤无垠的茄子地走去。
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一人多高的茄子植株后面,再也没有出现。操场上很快就空了。
我走到那台被遗弃的相机旁,将它捡了起来。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用陈宇留下的药水,
把那张照片洗了出来。照片上,三十个孩子笑容灿烂,嘴巴却都诡异地咧到耳根。
他们的嘴里,塞满了黑紫色的、还在微微蠕动的茄子。而在照片的最后排,角落里,
站着面无表情的我。我的嘴紧紧闭着。我默默地看着照片,直到眼睛发酸。然后,
我收起那张合照,把它和我藏在床底木匣子里的其他二十九张,整齐地叠在了一起。每一张,
都来自一届毕业的学生。每一张,都是一个外来者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我们村的秘密。
3. 残次品的秘密陈宇被关在祠堂的第三天,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嘶吼,
只是抱着头缩在角落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茄子……都是茄子……
我提着饭盒进去的时候,他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清明。林晚……
他挣扎着爬过来,抓住我的裤脚,你早就知道,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把饭盒放在地上:我告诉过你,是你自己不信。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拍照不能喊茄子?他凄厉地笑了起来,你应该告诉我,那些孩子根本不是人!
他们是怪物!他们不是怪物。我蹲下身,平静地看着他,他们只是……种子。
陈宇的笑声戛然而止。种子?是『神』的种子。我看着祠堂外那片紫黑色的田地,
声音飘忽,我们的神,就沉睡在那片地底下。而村里的孩子,就是为祂培育的容器。
每隔一段时间,神就会赐下种子,由村里的女人孕育。这些孩子生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们长得快,学东西也快,但他们没有未来。他们的宿命,就是在『毕业』那天,
被体内的种子吞噬,然后回归土地,成为神的一部分,换取村子的安宁和下一轮的丰收。
陈宇呆呆地听着,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那……那句『茄子』……是咒语,是钥匙。
我说,是唤醒他们体内种子的命令。只有外来者的声音,才能激活它。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村里就需要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师,来完成最后的仪式。
所以……从我踏进村子的第一天起,一切都是个骗局?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他瘫倒在地,眼神空洞,
嘴里喃喃自语:骗局……都是骗局……三十个孩子……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林晚。
他忽然叫住我,那你呢?你也是……种子吗?我的脚步顿住了。我转过身,看着他,
第一次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我是个残次品。我是三十年前,
那一届毕业的学生。我的母亲不是村里人,她是和我父亲私奔到这里的。
她不知道村里的秘密,直到她怀上了我。三十年前,
来的也是一个和陈宇一样满怀理想的年轻老师。毕业那天,他也让全班喊了茄子。
所有的孩子都毕业了,除了我。咒语对我起了作用,但并不完全。我没有被种子吞噬,
只是失去了生育能力,并且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村子。我成了一个异类。一个活着的毕业生
。村长说,这是神的旨意。让我留下来,作为村庄秘密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于是,
我成了林会计,成了那个给一张张恐怖毕业照收尸的人。残次品……
陈宇重复着这三个字,忽然疯了似的笑了起来,哈哈哈哈,残次品!我们都是残次品!
我没有再理会他的疯言疯语,转身走出了祠堂。我知道,村长他们很快就要处理掉陈宇了。
就像处理掉前面那二十九个老师一样。他们会把他埋进茄子地里,让他成为最好的养料。
而我,将继续守着这三十张照片,在这个活死人墓里,等待下一届学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