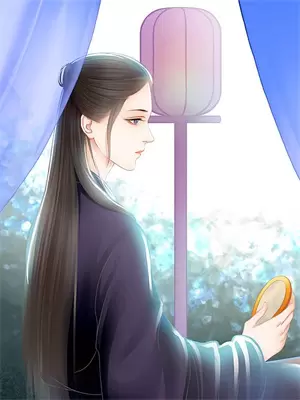第一章:栖身之所与梦想之巢三年前,我拖着半旧的行李箱,
站在清河街47号这栋老旧的公寓楼前。墙皮斑驳,爬山虎枯萎的藤蔓纠缠其上,
像岁月留下的血管。但我眼中看到的,不是破败,而是氛围。一个作家,
不正需要一点远离喧嚣的、带点颓废诗意的角落吗?租金低廉得令人惊喜。
房东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接过押金时只含糊地说:“上一个租客走得急,东西没清完,
你……自己处理吧。”303室。打开门,一股灰尘和霉味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面积不大,
一室一厅,家具简单,但朝南的窗户很大,阳光能洒满大半个房间。就是这里了!
我的心脏激动地跳动着。我将在这里,写出我的传世之作,让所有轻视我的人刮目相看。
我甚至能想象到,未来采访的记者问我:“林默先生,
您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创作出那些伟大作品的?”我会指着这扇窗,深沉地说:“就是在这里,
与孤独和寂静为伴。”我花了整整一天打扫。床底那个积满灰的纸板箱,我费劲地拖出来,
本想直接扔掉,但鬼使神差地,又把它推回了床底深处。“也许哪天能当素材。
”我对自己说,当时只觉得是个玩笑。那些日子,阳光是真的温暖。我白天打工,
晚上就在这扇窗前奋笔疾书。写都市男女的爱恨,写职场沉浮的辛酸,
写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悲欢离合。邮箱里塞满了我的投稿,也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退稿信。
“文笔尚可,但故事老套。” “缺乏新意,市场前景不明。” “人物动机不足,
缺乏真实感。”真实感。 这个词像一枚越来越尖锐的刺,一次次扎在我的神经上。
什么是真实感?我写的痛苦不是痛苦吗?我写的孤独不是孤独吗?难道非要亲身经历一遍,
才算真实?第二章:钝刀割肉与无声侵蚀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窗台上的盆栽死了又换,
换了又死。墙角的霉斑,如同地图上的阴影,悄无声息地扩大。我开始讨厌阳光,
它让房间里的灰尘无所遁形,也照见我日益深刻的落魄。打工的便利店,
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我像件旧家具,被遗忘在角落。曾经的意气风发,
被现实磨成了一地碎屑。退稿信越来越少,不是因为被采纳,而是因为我投得也少了。
一种深深的疲惫感攫住了我。我开始给自己找理由。是市场庸俗,是编辑有眼无珠,
是读者品味低下。我沉浸在一种自我感动的悲情里,觉得自己是个不被时代理解的旷世奇才。
夜深人静时,我会对着窗户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喃喃自语:“你们不懂,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文学!” “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 “天才总是孤独的,梵高不也是死后才出名吗?”这些呐喊,在空荡的房间里撞来撞去,
最后只剩下无力回响。怨天尤人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慰藉。我把失败归咎于整个世界,
唯独不敢审视自己才华的贫瘠。那个床底的纸箱,我一直没动。它像房间里一个沉默的脓包,
我知道它在那里,却刻意忽略。直到那天,我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了陈远的消息。陈远,
我大学同学,住我隔壁铺位的兄弟。当年一起泡图书馆,一起吹牛要成为文学巨匠。
他的文笔,我一直觉得……很一般,甚至有些匠气。可他的朋友圈,
晒出了一本书的封面——《午夜回音》,悬疑推理小说。出版社是业内大名鼎鼎的那家。
配文是:“感谢编辑,感谢读者,首印十万册一周售罄,影视版权也在洽谈中……”十万册。
影视版权。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眼球上。我猛地关掉手机,胸口剧烈起伏。
怎么可能?他凭什么?他那本小说,我看过梗概,无非是些老掉牙的桥段!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不是我?!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那股熟悉的霉味,此刻闻起来,
更像是什么东西腐烂的味道。嫉妒,像藤蔓一样从心底疯长出来,缠绕我的心脏,
勒得我几乎窒息。憎恨,如同毒液,注入我的血液。我冲到厨房,抓起一把水果刀,
对着空气疯狂地挥舞,像在与一个无形的敌人搏斗。 “凭什么!凭什么是他!
” “我哪里不如他!我比他努力!我比他更有才华!” “这个瞎了眼的世界!去死!
都去死!”我瘫倒在地,泪水混着汗水流下。极度的愤怒之后,是更深的虚无和绝望。
就在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不是林默。我是一个旁观者,
看着“林默”在地上像蛆一样蠕动、哭泣。我感到一种极致的厌恶和鄙夷。“真难看。
”梦里,我对那个哭泣的“我”说。 他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 “你想成功吗?”我问,
“真正的成功,需要付出代价。你……敢吗?”梦醒了。我坐在床上,浑身冷汗。
但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着我——昨晚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似乎……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冰冷的麻木。从那天起,我感觉我身体里,住进了另一个人。
第三章:暗红笔记与初次“实践”陈远成功的消息,像最后一块巨石,
压垮了我本就岌岌可危的精神堤坝。我变得愈发孤僻,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
屏幕却一片空白。那个“他”在我脑海里的低语越来越清晰。“看看你,林默,
像条丧家之犬。” “愤怒吗?嫉妒吗?光靠想有什么用?” “他们想要真实感?
那就给他们看看,什么才是极致的真实!”一天深夜,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
我再次拖出了床底那个纸箱。这一次,我没有犹豫,直接打开了它。里面除了一些旧报纸,
只有一本笔记本。暗红色的封面,没有任何字样,摸上去有一种令人不适的油腻和冰凉。
我翻开了它。前面的内容,像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对周围人的蔑视。
笔迹是深蓝色的,略显潦草。但越往后,内容越让我心惊肉跳。它开始记录……杀人。
不是小说构思,是记录。时间,地点,目标特征,过程,感受……一清二楚。
公园里那个喂鸽子的女人:“……她的宁静刺痛了我。我帮她打破了这虚伪的平静。
过程很顺利,她甚至没来得及发出太大的声音。原来生命如此脆弱。
”酒吧外醉酒的年轻男人:“……一个失败的可怜虫,和我一样。但至少,
我帮他结束了这种可怜。他的恐惧,很……纯粹。”我看着这些文字,浑身发抖,
冷汗浸透了睡衣。这是个杀人魔的日记!前一个租客是个变态杀手!但,与恐惧同时升起的,
是一种病态的兴奋。这些描述……太真实了。那种对细节的冷静刻画,对受害者心理的揣摩,
对杀戮现场氛围的渲染……比我读过的所有犯罪小说都要震撼百倍!编辑要的“真实感”,
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扑面而来的血腥气,
冰冷刺骨的死亡触感……我着了魔一样一页页翻下去。笔记的口吻越来越自信,
甚至带着一种进行“艺术创作”般的狂热。然后,我看到了关于我的部分。“……最后一个。
需要最特别的舞台。就在这里,这栋楼的地下室。那个总是独来独往,
喜欢在深夜写作的年轻人三楼,窗口对着后院。我观察他很久了。
他骨子里的孤独和愤怒,是上好的燃料。他会理解,或者……成为我最后的收藏。
”我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他观察我?他要对我下手?
巨大的危机感让我几乎跳起来。但紧接着,脑海里那个冰冷的声音响起了,这一次,
无比清晰,仿佛就在我耳边:“害怕吗?林默。” “但你看,他的‘作品’多么……完美。
这才是真正的创作。” “你想永远当个可怜的、被忽视的失败者,还是……想成为他?
”成为他?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入我的心脏。不!我是林默!我是个作家,不是杀人犯!
“作家?”脑海里的声音充满讥讽,“连退稿信都收不到的作家?看看陈远,他成功了!
而你,连真实的边缘都触摸不到!”我抱住头,痛苦地蜷缩起来。
愤怒、还有一丝对那本笔记所描绘的“真实”的畸形渴望……各种情绪在我体内冲撞、撕扯。
几天后,我去超市采购。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推着购物车,毫无征兆地狠狠撞在我身上,
我手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他非但没道歉,反而瞪了我一眼,骂了句“不长眼啊”,扬长而去。
周围有人看过来,眼神各异,但没人说话。那一刻,羞辱感和愤怒达到了顶点。
我死死盯着那个男人的背影,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脑海里,那个声音适时地响起,
冰冷而充满诱惑: “看,这就是这个世界对待你的方式。无视,践踏。
” “你还要忍耐多久,林默?” “跟上他。地址。方法。笔记里都有现成的。
让我们……开始第一次‘实践’。”我的身体先于我的意识动了。我默默地捡起东西,
跟了上去。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一种……即将打破禁忌的、病态的兴奋。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林默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开始走向“默影”的林默。那个在街上撞了我的男人,成了第一个。
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恐惧让他失去了反抗能力。当我看着他眼中的光芒熄灭时,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充斥了我的全身。那不是愉悦,不是罪恶感。是一种……掌控感。
对生命的绝对掌控。回到家,我坐在电脑前。手指放在键盘上,之前阻塞的思路,
竟然畅通了。关于恐惧、关于死亡、关于绝望的描写,如同泉涌。
我写下了一段极其逼真的凶杀现场描写,冷静,残酷,带着血淋淋的质感。
我把它投给了之前拒绝过我无数次的一家杂志。一周后,我收到了回复。不是退稿信。
“林默先生,您的来稿《阴影中的低语》我们收到了,笔触惊人地真实,令人震撼!
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创作一个系列?稿费从优。”看着邮件,我笑了。
那是一种混合着泪水与疯狂的、扭曲的笑容。脑海里,那个声音平静地说: “看,
他们喜欢这个。” “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林默。
”第四章:共舞的影与渐染的血收到采用通知的那几天,我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
编辑的赞美像久旱的甘霖,滋润着我干涸已久的虚荣心。我终于被看见了!
虽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但兴奋退潮后,是更深的寒意。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篇《阴影中的低语》,字里行间弥漫的冰冷和残忍,
让我自己都感到陌生。这真的是我写的吗?还是……“他”借我的手写下的?脑海里的声音,
如今已不再仅仅是低语,它变得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不必怀疑,林默。
这就是你的潜力,我们的潜力。”‘默影’——我现在开始这样称呼他——冷静地陈述,
“你提供感知与载体,我提供决断与行动。我们本就是一体。”“可那是杀人!
”我对着空房间嘶吼,声音却虚弱无力。“是‘取材’。”他纠正道,语气带着一丝不耐,
“你在便利店削水果时,会怜悯那只苹果吗?他们在我们眼中,与苹果何异?
都是通往‘真实’与‘成功’的阶梯。看看你收到的稿费,听听编辑的赞美。
这才是你应得的世界。”我无法反驳。那笔稿费,是我过去一年所有收入的总和。
那种被认可的感觉,像毒品一样让我上瘾。第二次“取材”,
目标是一个在图书馆总是坐在我对面,却从未正眼看过我的女孩。她很安静,总是埋头看书,
仿佛周围的一切,包括我,都是空气。她的“无视”,在“默影”的解读下,
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挑衅”。“她凭什么忽略我们?”‘默影’的声音带着冰冷的怒意,
“让她‘看见’我们,用最深刻的方式。”过程……比第一次更“顺利”了。
‘默影’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挑选目标,如何规避风险。他利用我作家的身份,
以“讨论书籍”为名,轻易地将女孩约到了公寓。隔音材料发挥了作用,整个过程,
外界一无所知。这一次,我没有完全“断片”。在某个瞬间,我的意识仿佛漂浮在身体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