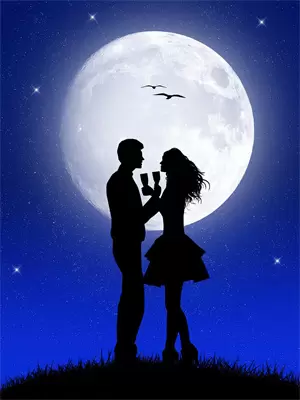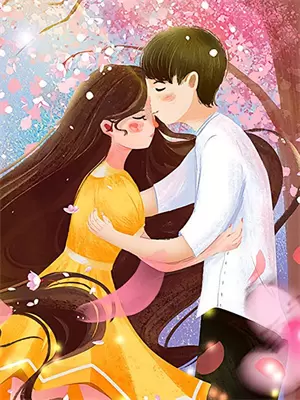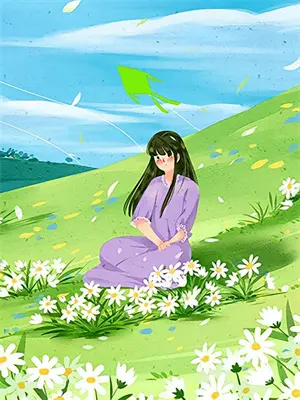
1 新婚燕尔,心如寒冰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金陵城的桂子开得泼泼洒洒,
满城都浸在甜腻的香里,可这香气却像一层薄薄的糖衣,
裹不住时局动荡下那若有似无的不安。秦公馆里张灯结彩,大红的“囍”字贴满了雕花廊柱,
西洋乐队的旋律与中式唢呐的调子混在一起,热闹得有些刻意。
沈怀瑾身着一身繁复沉重的大红喜服,
端坐于秦家精心打造的西式婚房里那张格格不入的雕花拔步床上。
头顶的红盖头绣着金线鸳鸯,隔绝了她的视线,只听得见窗外隐约传来的宾客喧闹,
以及自长江码头方向飘来的、若有似无的轮船汽笛声——那声音像一根细针,
轻轻刺着她对未知的忐忑。她与秦风的婚事,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沈家虽是没落的书香门第,可祖上出过翰林,家风清贵,
是秦家用多少银元都买不来的体面;秦家是新兴的实业巨头,家底雄厚,
却急需文化装点门面,更需要在政界寻得可靠盟友。这场联姻,
在旁人看来是珠联璧合的美事,于沈家是“攀附”,于秦家是“体面”,各取所需,
唯独没人问过她沈怀瑾愿不愿意。出嫁前一夜,母亲拉着她的手垂泪,
指尖的凉意透过锦缎嫁衣传过来:“秦家势大,规矩多,我儿过去,凡事忍耐,
谨守妇道……”怀瑾望着镜中一身红妆的自己,心中既有对陌生环境的忐忑,
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憧憬——那个据说留洋归来、在财政部身居要职的年轻丈夫,
会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像书中写的那样,有一双藏着星辰的眼睛?脚步声由远及近,
沉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虚浮,混合着淡淡的酒气,打破了房内的寂静。
房门被轻轻推开,又缓缓关上,那脚步声停在了她的面前。怀瑾的心猛地提起,
像被风吹得摇晃的烛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握着一杆包金的秤杆,
轻轻挑开了她头顶的喜帕——光线骤然涌入,她下意识地眨了眨眼,待视线清晰,
便撞进了一双深邃却如同古井般冷淡的眼睛里。她的新郎,秦家三少秦风,
穿着一身挺括的白色西装,胸前别着红绸礼花,身姿挺拔,相貌是无可挑剔的英俊。
可他眉宇间凝着的疏离,像一层厚厚的冰,让怀瑾心头刚燃起的那点小小火苗,
“噗”地一下彻底熄灭了。他看她的眼神,不像看新婚妻子,
倒像看一件刚从礼盒里取出来的、无关紧要的摆件。“累了就早些休息。
”他的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半分新婚的喜悦,也听不出厌恶,
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琐事。他甚至没有在她身边的拔步床上坐下,只是扫了她一眼,
便径直走向了衣帽间,换下西装,拿出一床薄被,
自顾自地在窗边的沙发上铺开——那沙发是西洋款式,宽大却冰冷,
与这满室的红妆格格不入。那一夜,红烛高燃,烛泪顺着烛台缓缓滴落,像无声的叹息,
映照着室内诡异而沉默的氛围。怀瑾和衣躺在宽大的婚床上,
身下的花生、红枣硌得人脊背生疼,却远不及心里的冰凉。她侧身望着窗外清冷的月光,
月光透过薄纱窗帘,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也照亮了沙发上那个陌生的身影。
她听着沙发上传来均匀却疏离的呼吸声,
泪水无声地浸湿了绣着鸳鸯的枕套——这就是她将要托付一生的人吗?这就是她的婚姻吗?
婚后的日子,是日复一日的“相敬如冰”。秦风是政府财政部的机要秘书,年轻有为,
却也忙碌得脚不沾地,常常深夜才归。他身上的气息总在变化,有时带着酒气,
有时带着脂粉香,更多时候是挥之不去的疲惫与冷漠。他从不与她谈论工作,
也不问她的日常,两人同处一室,常常是一整夜的沉默,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在空气中回荡。
怀瑾则努力适应着秦家少奶奶的身份,每日晨昏定省,伺候公婆;打理不算复杂的内务,
应对几位妯娌或明或暗的打量——她们看她的眼神,总带着几分“落魄小姐攀高枝”的审视。
她本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在燕山大学读医科,通晓中西医理,
曾梦想着毕业后开一家小小的诊所,救死扶伤。可如今,她却困于这方寸宅院,
学着插花、品茶,管理永远也对不完的账本,心中的苦闷,像潮水般涨落,却无人可诉。
转机发生在一个午后。秋日的阳光透过梧桐叶,在书房的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婆婆让她去书房给秦风送一碗参茶,他恰好不在。怀瑾放下茶碗,
目光被书架最高层几本显眼的旧洋装书吸引——那是几本英文原版书,封面已经有些磨损,
与书架上一排排精致的线装书截然不同。鬼使神差地,她搬来一张小凳子,
踮起脚尖抽出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书页刚翻开,
一张边角已微微卷曲的黑白照片便从书中抖落,飘落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地板上。
怀瑾弯腰拾起照片,心脏猛地一跳。照片上的女子明眸皓齿,剪着利落的及耳短发,
穿着素雅的月白色旗袍,外罩一件米白色的西式针织开衫,站在大学校园的银杏树下,
笑容自信飞扬,眼神清澈而坚定,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照片背面,
是一行清秀却力透纸背的钢笔字:“愿以此身报家国,此生不必再相见。
——晚晴”“苏晚晴……”怀瑾轻声念出这个名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呼吸都停滞了一瞬。她听说过这个名字,在秦家的丫鬟婆子闲聊时,
在秦风偶尔醉酒后的呓语里。她是秦风在燕京大学时的恋人,
一位才华横溢、积极投身救国运动的风云人物,曾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言辞犀利,
风采灼人,引得无数青年追捧。原来,他们并非和平分手,而是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
被迫决绝离别。看着那行字里行间透出的刚烈与决然,怀瑾的心像是被细密的针扎了一下,
不是嫉妒,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深沉的悲哀。那个如同火焰般耀眼的女子,
选择了挣脱束缚,奔向更广阔的天地,用行动报效家国;而自己,
却像一只被精心饲养的金丝雀,被困在这锦绣牢笼里,为了家族的体面,
也为了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的丈夫,消耗着青春。她将照片小心翼翼地夹回书中原来的位置,
把书放回书架,又仔细抚平了书脊上的褶皱,仿佛什么也没发现。可有些东西,
已经悄然改变了。她走到书房的穿衣镜前,
看着镜中那个眉宇间带着轻愁、穿着精致旗袍却眼神黯淡的自己,
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她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2 各奔前程,殊途同归不久后,
卢沟桥的枪声像一道惊雷,震动了整个华夏大地。战争的阴云迅速笼罩了金陵城,
往日的歌舞升平被骤然打破。报纸上触目惊心的战报,街头日益增多的流民,
以及空气中弥漫的恐慌与悲壮,取代了桂子的甜香,成了这座城市的主旋律。
怀瑾再也无法安心做她的秦少奶奶。插花时,指尖触碰花瓣,
却总想起报纸上那些流血的伤员;品茶时,茶水的清香里,仿佛也混杂着硝烟的味道。
这些曾经被她视为“少奶奶必修课”的事情,如今变得如此苍白无力。她终于下定决心,
在一次家庭晚宴上,向公公婆婆提出,要利用自己的医术,
去政府组织的伤兵医院或者红十字会帮忙。“胡闹!
”婆婆手中的象牙筷子“啪”地一声放在描金瓷碗上,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那种地方也是你能去的?脏乱不说,还有流弹,万一伤着了怎么办?”公公也皱紧了眉头,
放下手中的酒杯,语气严肃:“怀瑾,你是秦家的少奶奶,抛头露面去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成何体统?传出去,别人会说我们秦家不懂规矩。”怀瑾端坐在餐桌旁,
第一次没有像往常那样低头沉默。她挺直脊背,目光平静却坚定地迎上公婆的视线,
声音清晰而有力:“父亲,母亲,如今国难当头,多少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
我辈岂能安坐后方,贪图安逸?我在燕山大学学医五年,本就是为了济世救人,
如今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秦家乐善好施,在金陵城素有美名,若儿媳能去救助伤兵,
既能践行医者仁心,于家族名声亦是有益无害。”她搬出了“家族名声”,
又恰逢全民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秦家权衡再三,最终勉强应允了她的请求,
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必须带着贴身丫鬟和两个男仆同行,且只能在后方的伤兵医院工作,
绝不可去危险的前线。走进伤兵医院的那一刻,怀瑾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她脱下华丽的旗袍,换上朴素的蓝色粗布护士服后来因她医术精湛,且医院医生紧缺,
被破格允许参与一些小型手术,将一头乌黑的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
用一根简单的木簪固定。这里没有风花雪月,只有血腥、痛苦和死亡。
她清秀的脸上常常沾染着血污,纤细的手指因长时间浸泡在消毒水中而发白、起皱,
甚至裂开细小的伤口,可她那双原本带着轻愁的眼睛,却日益明亮、坚定。
她手法娴熟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冷静地协助医生进行手术,
温和地安抚那些因疼痛而嘶吼的士兵。在绝望的呻吟与震天的炮火声中,
她瘦弱的肩膀仿佛能扛起一片天,成了伤员们眼中的“沈大夫”,
而非那个养尊处优的“秦少奶奶”。也就是在这里,她再次听到了苏晚晴的消息。
一位来自前线的护士偶然提起,说有个叫苏晚晴的女同志,是某个重要救亡团体的骨干,
正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奔走,负责物资筹措与人员转移,几次遭遇日军的搜查,
险些被捕。怀瑾握着止血钳的手顿了顿,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敬佩,
还有一丝莫名的牵挂。命运的齿轮,总在不经意间转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金陵城被乌云笼罩,雷声滚滚,医院的救护车呼啸着冲进雨幕,
接回了一批从徐州前线转运来的重伤员。怀瑾穿着雨衣,在急诊室门口帮忙接应,
当担架床被抬进来时,她的目光骤然凝固——担架上那个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女子,
正是她在照片上见过的苏晚晴。据护送的同志说,
她是为了保护一批进步学生和重要的宣传资料,遭遇了敌机空袭,腹部中弹,失血过多,
生命垂危。怀瑾认出她时,心中巨震,仿佛有无数根线在拉扯着她的神经。
但医生的本能让她立刻冷静下来,所有的情绪都被压在了心底。“快!准备手术!
”她厉声吩咐护士,亲自推着担架床,快步冲向手术室。无影灯亮起,
手术刀划破皮肤的瞬间,她的手没有一丝颤抖——此刻,她不是秦少奶奶,不是秦风的妻子,
只是一名医生,要救另一个为家国而战的女子。手术室门口,闻讯赶来的秦风浑身湿透,
雨水顺着他的头发、脸颊往下淌,滴落在白色的地砖上,晕开一片片水渍。
他脸色是从未有过的苍白和惊慌,平日里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前,
眼神里充满了焦虑。他几乎是踉跄着冲过来,试图闯入手术室,
却被刚刚完成初步止血、满手是血的怀瑾拦住。“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