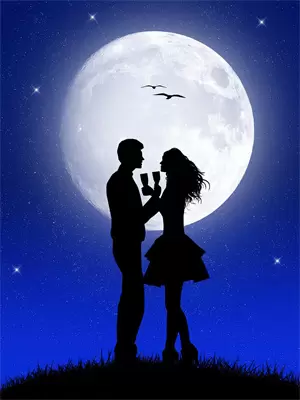林晓雨搬入钟鼓楼旁那套老城区出租屋时,暮色已将檐角染成暖黄,
巷口糖炒栗子摊的铁铲正反复翻搅,焦香混着煤烟味在微凉空气里漫开,
最后像细丝线般缠在她拎行李箱的手腕上,裹着市井独有的烟火暖意。
领路的中年中介穿件洗得发白的旧西装,袖口沾着未擦净的蓝黑墨迹,裤脚卷两圈,
露出沾泥的白球鞋,鞋尖还磨出个毛边。两人踩着七层水泥楼梯上行,
每一步都震得铸铁扶手微微发麻,转角的声控灯接触不良,被脚步声惊醒后忽明忽暗,
橘黄光晕里,墙上“小心地滑”的标语早已泛黄起卷,
旁侧留着孩童用白粉笔涂鸦的歪扭小人,手里举着根不成形的棒棒糖。
钥匙在锈迹斑斑的锁孔里转了三圈,伴着齿轮错位的滞涩声,才“咔嗒”一声沉钝作响。
屋门开启的瞬间,灰尘、旧布料与时光交织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她下意识捂鼻。
中介攥着卷边的合同,指节泛白,喉结急促滚动,翻来覆去就那一句:“月租五百,
押一付一,这片区再无二家。”他的目光总若有似无瞟向卧室墙角——林晓雨顺着看去,
那片水渍像幅晕开的抽象画,边缘泛着青灰,竟隐约是片蜷缩的银杏叶,
叶脉纹路都清晰可辨。她追问缘由,中介慌忙别过脸,双手在西装下摆蹭了又蹭,
喉结再滚一圈,含糊搪塞:“老房潮气重,开窗通三天风就好,之前租客从没说过有问题。
”说罢把笔往她手里塞,指腹点着签名处催得急,笔尖划过纸面都带着仓促,
连日期都险些写错。这顶楼的屋子遭西晒多年,墙皮斑驳如陈年陶片,裂纹里嵌着积年灰尘,
深处藏着几粒褪色墙屑,干纹纵横得像老人手背的褶皱。墙角悬着几缕蛛网,
沾着细碎棉絮与不知哪年的梧桐絮,风一吹就轻轻晃。
楼道转角堆着邻里废弃的旧衣柜和藤椅,藤椅缝卡着片干枯发黑的梧桐叶,
椅面还留着半道孩童刻的“小太阳”;常年不见光的角落滋着青黑苔藓,
指尖一碰就沾着湿润绿痕,裹着泥土腥气。潮湿霉味与老木沉香缠在一起钻进鼻腔,
竟奇异地透着陈旧暖意。可对刚毕业、攥着三千块实习薪资,
扣完通勤费和伙食费只剩八百结余的林晓雨来说,这租金不啻于救命稻草。
她捏着皱巴巴的五百块定金,指腹摩挲着纸币起毛的边缘,指尖泛白。抬头望时,
钟鼓楼的飞檐已浸在暮色里,远处传来最后一班公交“前方到站钟鼓楼南”的报站声,
裹着电流杂音。她深吸一口满是老房气息的空气,咬牙在合同末尾落下名字,
笔尖划过纸面的瞬间,生出几分背水一战的决绝——这笔租金,
是她在这座钢铁森林里站稳脚跟的最后底气。从楼下便利店搬完最后一箱泡面和矿泉水,
林晓雨瘫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歇气,汗水顺着额角滑进衣领,激得她打了个轻颤。
借着窗外透进的路灯光,她开始收拾:行李箱里的衣物要一件件挂进吱呀作响的旧衣柜,
衣柜门早没了铜拉手,得用指节抠着门板边缘使劲拽才能拉开,
柜壁还贴着张泛黄的2015年日历,日期停在“6月1日”。褪色的窗帘洗得发白,
透光性好得过分,挂在生锈的罗马杆上总往一边滑,她翻遍行李箱找出根红色晾衣夹固定,
夹子上还留着家里阳台的阳光味,隐约飘着皂角清香。带来的折叠桌撑开摆在窗边,
桌腿晃得厉害,她从楼道捡了块平整硬纸板垫在底下,才算稳住。
桌上摆上从学校带回的马克杯——杯身校徽早已模糊,杯沿缺着个小角,
是当年社团活动的纪念品;还有几本卷边的专业书,扉页印着大学导师的赠言,
这才勉强有了点“家”的模样。收拾到深夜十一点,窗外钟鼓楼的最后一声钟鸣荡开,
余韵在巷子里绕了三圈,才被远处的狗吠打散。林晓雨泡了碗红烧牛肉泡面,热水冲开时,
热气模糊了眼镜片,她摘下用袖口擦净,就着热气匆匆吃完,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暖融融的汤汁滑过肠胃,驱散了些许疲惫。她躺上铺着旧褥子的床,被褥是从家里带来的,
晒过午后太阳,残留着棉絮与阳光的混合暖意,倦意像潮水般漫上来,眼皮重得像坠了铅。
就在意识即将沉底时,
一阵突兀的声响像尖针般扎进耳膜——那声音从卧室邻侧的储物间飘来,“吱——呀——”,
绵长干涩,分明是细瘦的指甲在糙砺墙面上执拗地游走,每一下都带着刻意的停顿,
像个孩子攥着细瘦的指甲,在糙砺墙面上执拗地游走,又像在传递某种隐秘信号。
午夜的寂静里,这声响格外清晰,甚至能听见指甲划过墙皮时,细碎墙屑簌簌掉落的轻响,
如细针般钻入耳膜,直往心脏里扎。林晓雨猛地睁眼,黑暗中只有窗外路灯投来几缕昏黄,
在地板上拖出长长的斜影,像极了外婆讲的鬼故事里“影子抓人”的桥段。
她下意识裹紧薄被,脑袋往枕间缩,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指尖冰凉地攥着被角,指节泛白,
连呼吸都不敢太重,生怕惊动了门外的“东西”。这声响断断续续缠磨了近一个时辰,
时而轻缓如耳语,仿佛怕惊扰谁;时而突然加重,带着几分委屈的急促,
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巷口早点摊支起铁锅的叮当声、油条下锅的滋滋声,
还有摊主“刚出锅的油条嘞”的吆喝声传来,才终于消散。次日清晨,
林晓雨顶着熊猫似的黑眼圈在储物间门口徘徊,门把手上还留着她昨晚摸索时的淡青色指印。
她反复劝自己是老鼠作祟,或许是哪只胆大的老鼠在啃墙内木筋,
可指尖触到储物间冰凉的墙面时,
忽然想起搬入时特意叩过这墙——厚实的砖墙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别说老鼠,
就是成人挥拳猛击,也砸不出这般有节奏的动静。她蹲下身,指尖拂过墙根缝隙,
只摸到些干燥墙屑,没有鼠洞,缝隙里卡着半片干枯梧桐叶,叶边卷着,
不知是哪年被风吹进来的。往后一周,这叩墙声成了林晓雨的午夜梦魇。
它每晚准在子时响起,分秒不差,仿佛有只无形的时钟在暗中操控,比手机闹钟还准时。
第一晚的惊恐过后,林晓雨试过蒙头睡,把被子叠成双层捂耳朵,可那声音总能穿透棉絮,
像幽灵般在耳际盘旋;她又开着床头灯睡,橘黄灯光照亮卧室一角,梳妆台的影子投在墙上,
竟像个站立的人影,却照不进储物间的门缝,反倒让黑暗中的声响更显诡异,
仿佛门后正有双眼睛透过缝隙注视着她。她被折腾得精神恍惚,白天上班频频走神,
对着电脑表格发呆,光标闪了半天,竟忘了要输什么数据。邻座的张姐见她脸色不对,
悄悄塞来一块巧克力,关切地问:“是不是没休息好?”她勉强牵起嘴角,含糊应了声。
咖啡一杯接一杯地灌,苦涩液体烫得食道发疼,却挡不住眼底的青黑与倦意,
连主管交代的季度报表都填错了三个关键数据。主管把她叫进办公室,指尖叩着报表纸,
眉头拧成道深川:“晓雨,你平时挺细心的,最近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有困难就说,别硬扛。
”她攥着衣角支支吾吾,脸涨得通红,只能反复道歉:“我马上改,马上改。
”周五在茶水间接热水时,她因走神被滚烫的水烫到右手食指,钻心的疼让她瞬间红了眼,
积压一周的委屈与恐惧终于决堤。她躲进消防通道,背靠着冰冷的铁门拨通物业电话,
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您好……我家储物间……每晚都有怪声……能不能来看看?
”维修师傅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额角刻着老树皮似的皱纹,扛着沉甸甸的工具箱赶来,
铁盒碰撞着发出“叮当”响。他进门后先绕屋转了圈,鼻尖嗅了嗅,
随口道:“这房比我儿子还大,我年轻时候帮房主修过水管,那时候墙刚砌好没多久。
”进了储物间,他掏出小锤,沿着墙缝一寸寸敲验,耳朵贴墙细听,时而皱眉,时而点头,
还掏出粉笔做了几个标记。半个钟头后,他直起身捶捶发酸的腰,皱眉摇头:“姑娘,
这墙结实着呢,当年用的高标号水泥,连道细纹都没有。除非墙芯藏了东西,
可这是实心砖墙,这墙是我当年跟着老工匠一块砌的,一砖一瓦都扎实,绝无可能。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片水渍,蹲下身摸了摸,指尖沾着潮湿墙皮:“倒是潮气得注意,
天晴多开窗,别让家具发霉了。”林晓雨将信将疑,当晚绕了两条街去超市买捕鼠夹。
货架上的捕鼠夹从五块到二十块不等,她攥着钱包反复摩挲零钱,
犹豫半天选了三个最便宜的大号款。货架旁的导购阿姨见她面色苍白、眼下青黑,
关切地问:“没休息好?买点安神牛奶吧,睡前喝睡得香。”她强撑着笑摇头:“不用了,
谢谢阿姨。”回到家,她在储物间墙角、门边摆好捕鼠夹,
每个夹上都搁了块肥瘦相间的熏肉——那是她上周买的,舍不得吃一直冻在冰箱里,
还在地上撒了些面包屑,布下“天罗地网”。可次日清晨查看时,捕鼠夹纹丝未动,
熏肉上落了层细灰,旁侧散落着几片灰褐色墙屑。更让她心头发紧的是,
储物间那面有水渍的墙上,靠近踢脚线处多了道新浅痕——短短两寸,边缘带着不规则锯齿,
弧度圆润,活像孩童用指甲划的,与前几日的三道痕迹并排着,像串未完成的密码,
又像在默默计数,透着说不出的诡异。周末夜里,雨丝斜斜织着,在玻璃上洇出蜿蜒的水痕,
像谁在窗上画满泪痕,又像无数银蛇蠕动。潮湿气息顺着窗缝渗进来,让霉味愈发浓重,
还混着雨打梧桐叶的清苦,沉郁地压在胸口。
林晓雨裹着妈妈织的枣红色菱形花纹毛毯坐在床边——这是她上大学时妈妈特意织的,
带着家的暖意。手里捧着杯滚烫的姜茶,杯壁温度透过掌心传到四肢,
暖了皮肤却驱不散心底的寒。她盯着窗外雨景发呆,路灯的光透过雨幕,
在地面投下模糊光晕。忽然想起毕业时爸妈送她去车站的模样:爸爸拎着沉重的行李箱,
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妈妈拉着她的手反复叮嘱“天冷加衣”“别总吃泡面”,
眼眶忽然就红了。陌生城市的孤独与连日来的恐惧缠在一起,让她鼻子发酸,
眼泪险些掉进姜茶杯里。墙上挂钟的分针刚指向十二,那熟悉的叩墙声准时响起,
这回竟比往日更清晰,穿透力极强,像带着股执拗的劲儿要钻进骨头缝里,
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啜泣,细细软软的,像迷路孩童在暗夜低咽,
每声抽噎都裹着化不开的委屈,揪得人心疼。林晓雨盯着天花板,
听着声响在雨幕中愈发真切:时而急促如鼓点,诉说着焦急;时而轻缓如叹息,
藏着无尽失落。一周的恐惧与烦躁在这一刻爆发,她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