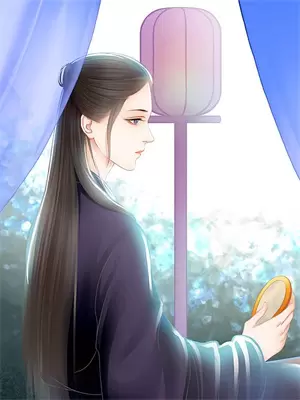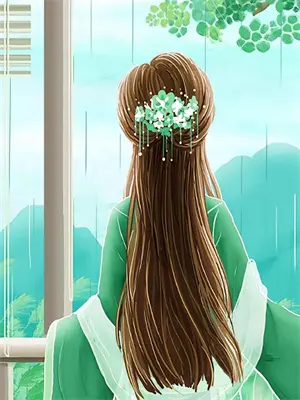
我变成老鹰后,发现城市上空笼罩着巨大的透明生物。它们以人类的负面情绪为食,
悄悄影响着所有人的行为。我的通缉令还贴在警局门口,但警察们正被这些生物操控。昨天,
我看见其中一个生物缠绕在我母亲身上,吸食她的担忧。今天,那只最大的生物,
停在了我最好的朋友肩膀上。而我,是唯一能看到它们的人。我被通缉了。谁也不知道。
我变成了一只老鹰。起初是撕裂般的疼痛,从骨头缝里钻出来。
我在那个肮脏的小旅馆房间里蜷缩着,听着楼下隐约传来的警笛声。
汗水浸透了我唯一的T恤。然后,痒,难以忍受的痒,
仿佛有无数羽毛正从我的皮肤下破土而出。我看着我的手指扭曲、变形,覆盖上坚硬的角质。
视野猛地拉宽、拉远,墙壁逼仄的纹路瞬间清晰得可怕。我想尖叫,
喉咙里却只挤出一声粗砺的啼鸣。我撞开那扇摇摇欲坠的窗户,玻璃碎裂的声音在身后远去。
城市的风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扑打在我新生的羽翼上。自由了。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
他们还在找我。为了那件我没做过的事。通缉令上的照片,印着我惶恐的人类面孔,
贴满了大街小巷,甚至就贴在警局最显眼的公告栏上。我偶尔会飞过那里,
锐利的眼睛能清晰地看到那张纸上每一个毛孔般的细节。可笑。他们追捕的那个“我”,
已经不存在了。飞行的感觉吞噬了一切恐惧。俯瞰下去,城市的脉络一清二楚。
灰白色的道路,积木般的车辆,蝼蚁样的人群。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但很快,
我发现了不对劲。城市的上空,并非空无一物。有一些东西。巨大的,透明的,
像扭曲的水母,又像是荡漾开的粘稠空气。它们缓慢地漂浮着,舒展着无形的触须,
轻轻搭在建筑物的顶端,或者,垂落下去,缠绕在那些行走的“蝼蚁”身上。
刚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是高空光线折射的错觉。
直到我盯着一只悬浮在十字路口上方的“东西”,仔细观察。它没有五官,没有固定的形态,
但当它下方因为堵车而响起一片刺耳喇叭声时,那东西透明的躯体似乎微微膨胀,
泛起一丝极其微弱的、满足般的涟漪。它在……进食?我降低高度,凭借老鹰完美的视觉,
聚焦于一个刚从写字楼里冲出来的男人。他挥舞着公文包,对着手机咆哮,脸涨得通红。
一股无形的、带着焦躁气息的波动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而一只稍小些的透明生物,
正趴在他的头顶,几条柔软的触须深深探入他的发丝,几乎埋进他的头皮。
随着男人的愤怒升级,那透明生物的轮廓似乎清晰了那么一瞬,
体型也微不可察地胀大了一点点。它以愤怒为食。这个认知让我浑身羽毛倒竖。
我疯狂地在城市上空盘旋,印证着我的猜想。争吵的夫妻窗外,趴着两只,
吸食着怨恨;拥挤的地铁车厢顶部,漂浮着一大片,享受着疲惫与麻木;医院上空,
聚集得尤其多,那些触须伸向下方,汲取着悲伤与恐惧。整个城市,
都被这些巨大的、透明的寄生生物笼罩着。它们悄无声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所有人的情绪,
甚至……行为?我想起我被指控的那桩谋杀。那个夜晚,巷子里的黑影,栽赃在我身上的刀。
目击者信誓旦旦地说看到了我的脸。当时我觉得荒谬,现在却感到一股寒意。那个目击者,
是不是也被什么东西缠绕着,被放大了内心的恐惧,或者篡改了模糊的记忆?警察们呢?
我飞过警局。不止是公告栏上的通缉令。那些进进出出的警察,肩膀上,头顶上,
或多或少都附着那些透明的东西。尤其是负责重案的那个老刑警,他的背上,
趴着一只格外肥硕的,触须深深扎进他的后颈。他皱着眉头,表情烦躁地训斥着下属。
他们被影响着。在它们的引导下,坚定地追捕着我这个“凶手”。我无处可逃,
也无处可申辩。谁能相信一只老鹰的话?更何况,
我还顶着一张被全城通缉的脸——虽然现在是羽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飞,观察,
以及……承受这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我是唯一能看到它们的人。不,唯一的鹰。这种清醒,
比蒙在鼓里更痛苦。昨天,我实在忍不住,飞回了那个我熟悉又陌生的旧街区。
我落在母亲公寓对面楼顶的水塔上,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她出来了。提着菜篮子,
背影有些佝偻。才几个月,她好像老了十岁。我的心揪紧了。然后,我看到了它。
一只中等体型的透明生物,像一件湿漉漉的、无形的厚重外套,紧紧缠绕在她身上。
它的几条核心触须,直接连在她的太阳穴和心口。它缓慢地、有节奏地搏动着,每一次搏动,
都从母亲身上抽取出淡淡的、灰白色的东西。那是担忧,是悲伤,
是对于一个失踪的、被通缉的儿子的无尽牵挂。母亲走得很慢,时不时抬手擦一下眼睛。
不是因为风沙。她在哭。而那个东西,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她的泪水凝结成的“营养”。
我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啸,猛地从水塔边缘腾空而起,双翅疯狂拍打,冲向那只生物。
我能撕裂野兔的爪子,能啄穿蛇皮的喙,却直接从它透明的身体里穿了过去。它毫无反应,
依旧紧紧依附在母亲身上,持续吸食着。母亲似乎被我的叫声惊动,抬起头,
茫然地看了一眼天空。她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它。她只看到一只发狂的野鹰。
她眼神里的空洞和悲伤,更深了。我失败了。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种无力感,
几乎要将我的翅膀折断。我在城市上空漫无目的地飘荡了一整夜,直到黎明再次降临。
我必须做点什么。任何事。我想到了阿杰。我最好的朋友。唯一一个在我“失踪”后,
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不相信我会杀人,呼吁大家冷静的朋友。他曾私下给我发信息,
说他会查清真相。也许……也许他可以。他是律师,有人脉,有头脑。带着一丝微弱的希望,
我朝着他工作的律所飞去。他通常很早就到办公室。
我落在律所大楼对面一座仿古建筑的飞檐上,目光锁定了他临街的办公室窗户。他果然在。
坐在办公桌后,手指快速敲击着键盘。阳光照在他身上,看起来一切正常。我稍微松了口气。
但下一秒,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个“存在”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窗外。它太大了。
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巨大。它的透明,带着一种沉重的质感,
像是一块流动的、扭曲的巨型水晶。它没有立刻动作,只是悬浮在那里,似乎在观察,
在选择。然后,它动了。它像一抹粘稠的液体,滑过玻璃窗,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墙壁和窗户,
进入了办公室。它没有像其他生物那样,随意附着在某个部位。它精准地,缓慢地,
落在了阿杰的左边肩膀上。阿杰敲击键盘的手指,停顿了一下。他微微皱了皱眉,
下意识地抬手揉了揉肩膀,仿佛觉得有些酸胀。他看不到。
那个巨大的、透明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东西,正稳稳地蹲踞在他的肩头。一条粗壮的触须,
像柔软的蛇,开始沿着他的脖颈,向上蜿蜒,轻轻触碰着他的太阳穴。另一条更细的触须,
则向下探去,似乎想连接他的心口。它在连接他。它在选择他。为什么是阿杰?
因为它感知到了阿杰正在调查,可能构成威胁?还是因为它需要借助阿杰的头脑和身份,
来做些什么?阿杰脸上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那种熟悉的、属于他的专注和温和,
正在一点点褪去。他的眉头锁得更紧,眼神里多了一丝我之前没见过的……阴鸷和烦躁。
他放在键盘上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它在放大了他的负面情绪?它在影响他的思维?不。
不仅仅是影响。我感觉,它是在“植入”什么。我看着阿杰,看着我最好的朋友。
看着那个巨大的透明生物,像一个邪恶的操纵者,牢牢占据着他的肩膀。通缉我的,
是这座城市看不见的规则,和那些被操控的警察。而此刻,正在侵蚀我唯一希望和慰藉的,
是这座城市上空,更庞大、更无形的恐怖。我是唯一能看到这一切的。我还是一只鹰。
我站在冰冷的飞檐上,锐利的目光穿透那层人眼无法察觉的透明,
死死盯住阿杰肩头上的那个东西。它的轮廓在城市的背景噪音里微微波动,
像隔着火焰看过去的景象。那根探向太阳穴的触须,已经稳稳地贴了上去,
细微的搏动顺着触须传递,像是在同步心跳。阿杰揉了揉额角,深吸了一口气,
重新将手放回键盘。但他的敲击声不再连贯,变得迟疑,甚至带着点粗暴的力度。
他在查什么?是在查我的案子吗?那个东西,是不是正因为他在接近某种真相,才找上了他?
一种冰冷的愤怒在我胸羽下积聚。我不能只是看着。我展开翅膀,悄无声息地滑翔下去,
绕着律所大楼盘旋。我需要更近一点,我需要知道它在做什么,阿杰又在做什么。
我找到了一处空调外机架,就在他窗户侧下方,视野有些偏,但足够近。
我能看到阿杰电脑屏幕的反光,能看到他紧抿的嘴唇。他在浏览新闻网页。
关于那起谋杀案的。通缉令我的照片,赫然挂在页面一侧。
他的鼠标在一个匿名爆料帖上停留了很久。帖子里暗示,有目击者受到了压力,
证词可能不准确。阿杰的肩膀动了动,他似乎想点击那个链接深入了解。
但就在他手指即将按下的瞬间,他肩头那巨大的透明生物,猛地收缩了一下。不是收缩,
是……发力?一股无形的波动荡开。阿杰的手指僵住了。他脸上的犹豫和探究,
像被橡皮擦抹去一样,迅速被一种强烈的烦躁取代。他猛地向后退开椅子,站起身,
在办公室里快速踱步。“浪费时间……”我听到他模糊的低语,透过玻璃传出来,
带着被放大后的焦灼,“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有什么用?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这话不像阿杰会说的。至少,不像以前的阿杰。他从来不会认为朋友的事是“浪费时间”。
是那个东西。它在扭曲他的想法,
放大他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一丝疲惫和怨怼?
还是直接灌输了这些念头?我死死盯住那透明生物。它似乎……更“清晰”了一点。
不再是完全融于空气,而是带上了一丝极淡的、污浊的微光。
它在享受这份被它催生出来的负面情绪。阿杰踱了几圈,又坐回电脑前。这次,
他没有再看那个爆料帖,而是直接关掉了网页,打开了一份复杂的案件卷宗。他的表情冷硬,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他要放弃调查我的事了?就因为这一下莫名的烦躁?不行。
我必须提醒他。怎么提醒?我是一只鹰。我无法说话,无法写字。
我焦躁地在空调外机上挪动爪子,金属支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阿杰若有所觉,
抬头向窗外看了一眼。他的目光扫过我藏身的地方,没有任何停留,又低了下去。
他看不到我。也看不到肩头的恶魔。我看着他重新投入工作,
肩膀上的东西似乎满意地微微起伏。那根连接太阳穴的触须,搏动得更加平稳了。
它在巩固这种状态。绝望像冰冷的雨水,浸透我的羽毛。我救不了母亲,现在,
连阿杰也要失去了吗?我在律所外守了一整天。看着阿杰处理公务,接打电话,会见客户。
他看起来依然专业,但那种偶尔流露出的、被强行压下的不耐,以及眼神里多出的冷硬,
让我感到陌生。那透明生物像长在了他身上,成为他影子的一部分。黄昏时分,
他离开了律所。我立刻跟上,在逐渐暗淡的天空中,保持着距离。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一家以前我们常去的酒吧。我落在酒吧对面街灯的灯罩上,
看着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威士忌。他一个人。低着头,看着杯中的琥珀色液体,
很久没有动。肩头的生物依旧在。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它似乎更“活跃”了。
触须轻轻摆动,像在探测周围环境的“情绪浓度”。
酒吧里弥漫着各种微妙的情绪:下班后的放松,约会的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