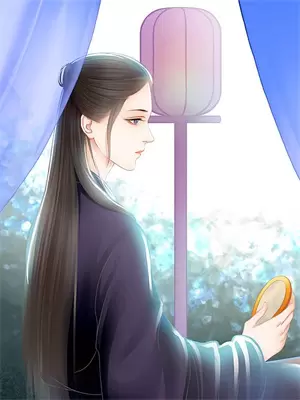我叫温玖,习惯走在阴影里,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直到那个午后,
我看见了一支不存在的送葬队伍,遗照上的少年对我微笑。车祸醒来,
他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阿玖,你忘了吗?我们曾相爱。”循着线索,我剥开记忆的茧,
却发现——我的人生,是一场由至亲以爱为名编织的、浸满鲜血的谎言。而真相的尽头,
站着亲手毁掉一切的我。---人行道的边缘,是我的安全区。肩膀擦着粗糙的墙面,
下班的人潮像浑浊的河水从我身边淌过。耳机里一片死寂,它只是我拒绝世界的盾牌。
项目经理李锐审视的目光,同事们窃窃的低语,都黏在背上,让人窒息。
我只想快点回到我那间小小的出租屋,用四壁的安静把自己包裹起来。红灯。
我停在那个走了无数次的十字路口,缩在等候人群的最边缘,
低头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帆布鞋尖。然后,世界失了声。车流声、人声,骤然被掐灭,
陷入一种粘稠的、压耳的死寂。空气凝滞,一股陈旧樟木混合冷香灰的陌生气味,弥漫开来。
我悚然抬头。心脏在那一刻骤停。一支队伍,正从横向的马路上,
无声地穿透亮起的汽车红灯。他们全都穿着粗麻布的白色孝衣,宽大、古朴,
样式老旧得像从泛黄的历史剧里走出来。没有哭声,没有乐声,连脚步声都听不见。
他们就那样沉默地移动着,动作带着一种非人的迟缓,
与周围流动的金属车壳、玻璃幕墙的反光,割裂成两个绝望的世界。寒意从脚底窜至头顶。
我想后退,脚却像钉在原地。队伍渐近,那阴森的死气几乎贴上我的面颊。我仓皇低头,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视线,就在这慌乱垂落的瞬间,
撞上了队伍最前方——那具没有加盖的深色棺椁前,端放着的黑白遗照。照片里是一个少年。
十七八岁的样子,眉眼干净,鼻梁高挺,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很好看。可我的血液,
在看清这张脸的刹那,彻底冻结。这张脸……我见过。不是模糊的记忆,
而是清晰的、带着寒意烙印。就在昨天深夜,我从溺毙般的噩梦中惊醒,去厨房喝水时,
无意间瞥见窗外——对面那栋废弃旧楼的楼顶边缘,
一个模糊的身影沐着惨淡的月光悄然独立。他微微侧过头,月光勾勒出的轮廓,
与眼前遗照上的少年,一模一样!怎么可能?!极致的恐惧攫住了我。
那支白色的送葬队伍与我擦肩而过,近得我能看清麻布纤维的粗糙,
能闻到那股愈发浓烈的、混合着腐朽与冷香的沉闷气息,几乎令我呕吐。“滋——!
”一股狂暴的、如同高压电流窜过大脑的尖锐鸣响猛地炸开!世界瞬间扭曲、剥离色彩,
只剩下吞噬一切的白噪音。我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
只觉得一股冰冷巨大的力量从侧面狠狠撞击而来。身体轻得像被狂风撕碎的落叶。
视野沉入浓稠的黑暗前,我涣散的瞳孔里,只烙印下那片渐行渐远的、荒谬的白色。然后,
一个清晰的、陌生的,却又诡异地牵动着某根神经的少年嗓音,穿透所有屏障,
精准地凿入我意识的最后壁垒。“阿玖。”---消毒水的气味顽固地钻入鼻腔。
意识在深海中挣扎上浮。睁开眼,是天花板和床边悬挂的、缓慢滴落的输液袋。“醒了?
”温和的男声在一旁响起。是穿着警服的王警官。他告诉我,撞我的司机找到了,
路口监控拍得很清楚——是我自己突然身体僵直,然后冲出了马路。没有任何送葬队伍。
他语气委婉,暗示可能是精神压力过大或脑震荡后的幻觉。幻觉?那真实的气息,
那清晰的面容,那刺骨的冰冷……“不是幻觉。”声音在脑海中响起。他说他叫沈予安。
三年前,他就死了。他说,从我能看见“他们”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命运就缠绕在了一起。
我必须帮他找到死亡的真相。否则,“下一次,就不会只是住几天院这么简单了。
”——出院后,沈予安的声音如同附骨之疽,盘踞在我的脑海。他不常开口,
但那无处不在的“存在感”本身就是最深的折磨。他用一种沉郁的深蓝墨水,
在我确定已锁好的日记本上,写下冰冷的指令:“路口东南角,槐树下。”恐惧驱使着我。
我在那棵老槐树下,挖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里面有一张泛黄脆硬的水果糖纸,
一枚内侧刻着模糊“S&W”字母的银色尾戒,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
是穿着校服的我与沈予安。我微微侧身低头,长发遮住大半张脸,身形僵硬。而他,
笑得一脸灿烂,手臂自然地搭在我肩上,低头看我的眼神,专注而深情。
“我们……真的认识?”声音干涩得厉害。“嗯。我比你低一届。阿玖,是我先爱上你的。
”他的声音有了一丝微弱的波动。记忆的迷雾似乎被拨开了一角。高中时,
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耀眼的学弟,家境优越,光芒万丈。可我们……紧接着,
一段更久远、更黑暗的记忆碎片,如同深水炸弹般在脑海引爆。那是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年幼的我蜷缩在客厅角落,看着父母又一次激烈地争吵、砸东西。母亲的哭喊,父亲的怒吼,
破碎的玻璃片溅到我的脚边。一种无法承受的恐惧和窒息感淹没了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眼前一片血红。我冲进厨房,拿起什么东西……后面的事,一片空白。只记得在医院醒来,
手臂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疼得钻心。父母守在一旁,眼睛红肿,布满血丝。他们告诉我,
是我不小心打碎了花瓶,被碎片划伤了。“玖玖以后要小心,知道吗?
都是爸爸妈妈没看好你。”母亲摸着我的头,声音沙哑,
眼神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愧疚。从那以后,父母再没在我面前吵过架,但家里的气氛,
总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小心翼翼的死寂。邻居们,亲戚们看我的眼神,
也总是带着那种欲言又止的怜悯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畏惧。这是我第一次“失控”。
代价是身上留下了莫名的疤痕,以及深植于心的、对冲突和目光的恐惧。
我开始习惯走在边缘,低头,不语。———在沈予安沉默的指引和断续的梦境中,
更多关于他的、带着暖意的记忆浮现。高二一个阳光慵懒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样,
躲在图书馆最角落的位置。“温玖学姐?”清朗的声音带着一丝犹豫。我抬起头,逆着光,
看见沈予安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两本书,笑容有些腼腆,耳根泛着淡淡的红。“好巧,
你也喜欢《追风筝的人》?”他像一束过于明亮的阳光,
不由分说地想要照进我灰暗封闭的世界。他会记得我随口提过的糖果,
下次见面时变魔术般掏出一把;会在下雨天固执地把伞塞给我,
自己冲进雨里;会在我因为家庭那令人窒息的气氛而沉默时,
用他笨拙却真诚的方式逗我开心。那温暖是真切的,灼烫着我冰封的心。
但另一段更为惨痛的青春记忆,也随之撕裂开来,
解释了为何我对这样的温暖既渴望又拼死抗拒。初中时,一个总是带着爽朗笑容的篮球队长,
像一簇火焰闯入我的生活。他会在我值日时帮我擦黑板,会在我被孤立时主动和我说话,
会给我带各种小零食。那种被关注、被善待的感觉,让我惶恐不安,
却又像溺水者抓住浮木般不肯放手。我沉浸在他编织的善意里,以为找到了救赎。直到那天,
我亲耳听见他在楼梯拐角,对着他的朋友们肆意嘲笑着我的孤僻和家境,
用轻佻的语气打赌多久能“拿下”我。那一刻,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猛地断裂了。
世界瞬间被染成血红。愤怒、羞耻、被背叛的痛苦如同岩浆喷发。
我抓起旁边消防柜旁的金属灭火器,
狠狠地、不顾一切地砸向他那张曾让我心动的脸……后面的事,再次模糊。
只记得父母又一次低声下气地赔了很多钱,家里气氛降至冰点。父亲摸着我的头,
那双常年带着疲惫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声音沙哑:“玖玖,是爸爸没用,
生意失败了……让你在学校受欺负了。以后……离那些人远点。”“生意失败”,
成了家里所有窘迫和我的所有“意外”的、统一的、苍白的解释。这是我第二次失控。
暴力倾向初显。从此,我更加将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不与人交流,
成了班里真正的“透明人”。面对沈予安执着而真诚的靠近,
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挣扎。他的眼神清澈,不似作伪,
但过去的创伤让我无法再相信任何善意。“为什么……偏偏是我?”我曾在一片黑暗中,
颤抖着问他。他的声音透过无形的连接传来,
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温柔:“因为在你坚硬的外壳下面,我看到了比谁都敏感和柔软的心。
阿玖,别怕,我只是想……温暖你。”——沈予安的指引,如同黑暗中唯一的丝线,
将我引向三年前关于“城西景辉苑工地意外坠亡”的零星报道。死者信息被严密保护。最终,
我独自一人,站在了那片荒废的、如同巨兽残骸般的烂尾楼群前。荒草蔓生,风声呜咽。
“是这里吗?”我轻声问,声音在空旷中消散。“第三栋,楼顶。”沈予安的声音低沉,
压抑着巨大的痛苦。攀爬着冰冷裸露的脚手架,每一步都如同迈向地狱。楼顶空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