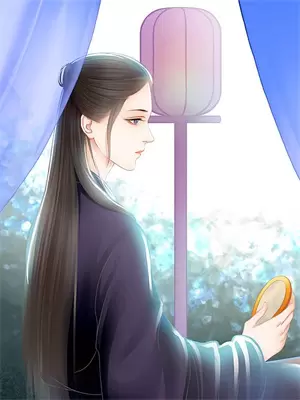噩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仍躺在初中宿舍的床上。
舍友悄悄告诉我:“你病了三天,学校颁布了新规——差生将被处决。”
我惊恐地发现枕边放着昨天“特殊考试”的准考证,上面用血字写着:不及格=挖眼+割舌+斩首。
更可怕的是,全校老师都变成了眼睛血红的监视者,而校门已经封锁。
我们必须伪装成优等生,在下次考试前找出学校的秘密...
---
头痛得像要裂开,每一次心跳都重重撞击着太阳穴,带来一阵阵沉闷的钝痛。我费力地掀开沉重的眼皮,视线花了十几秒才勉强聚焦。
映入眼帘的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属于清河初中男生宿舍301室的,泛黄起皮的天花板。空气里弥漫着那股特有的、混合了汗味、隔夜泡面汤和消毒水的气息。窗外,天光晦暗,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脏兮兮的灰布,看不真切具体时辰。
我……回来了?
记忆是断片的,最后清晰的画面,是三天前下午那场突如其来的高烧,数学课上老赵的喋喋不休变成了一串毫无意义的嗡嗡声,黑板上的公式扭曲旋转,然后世界就黑了下去。
之后是混沌的梦境碎片,光怪陆离,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甸甸的恐慌。但具体梦到了什么,此刻却一点也抓不住,只剩下心脏在肋骨后面失序地狂跳,擂鼓一般,印证着那恐慌并非凭空而来。
喉咙干得冒火,我挣扎着想撑起上半身,手肘却软得使不上劲,差点又摔回枕头上。这虚弱感真实得不容置疑。
“醒了?”
一个压得极低,带着气音的声音从旁边床铺传来。
我偏过头,是睡在我邻铺的李明。他侧躺着,面朝着我,被子拉到了下巴,只露出一双眼睛。那眼神不对劲,里面没有了往常的懒散和戏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力压抑的惊惶,以及……一种难以形容的警惕。他飞快地扫了一眼紧闭的宿舍门,又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把目光缩回来,牢牢钉在我脸上。
“你……你昏了三天了,”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更低了,几乎要散在空气里,“林默,出大事了。”
他的语气让那股刚被暂时压下的恐慌再次攫住了我。我没出声,只是用眼神询问。
“学校……学校颁了新规。”他吸了一口气,仿佛说出这几个字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关于……我们这种,‘差生’的。”
“差生”两个字,他吐得异常艰难。
我心里咯噔一下。成绩一直是我和李明,以及这间宿舍里大多数人的软肋。徘徊在及格线边缘是常态,老师的批评,父母的叹气,早已习惯。但李明此刻的反应,绝不仅仅是因为成绩差可能带来的常规惩罚。
“什么……新规?”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
李明没有立刻回答,他又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口,然后,极其缓慢地,几乎是一寸寸地,从他的被子里抽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那纸张的质地很普通,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考试答题卡那种粗糙的再生纸。
他用眼神示意我接过去。
指尖触碰到纸张的瞬间,一种冰冷的粘腻感传来,很不舒服。我展开它。
是一张准考证。
姓名:林默。班级:初一三班。考号:2023044……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直到我的目光落到最下方那一行用红色墨水打印的,额外附加的“考试须知”上。
那红色,鲜艳得刺眼,粘稠得像是刚刚凝固的血液。
“特殊学业测评须知:本次考试成绩将作为重要评定标准。评定不合格者,将视作无可塑之劣质品,予以即时的、不可逆的净化处理:第一阶段,摘除视觉与言语器官;间隔四十八小时后,执行第二阶段,生命体征终止。”
冰冷的、公文式的措辞。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同样是血红色的字,像是手写体的备注:
“净化流程:挖眼。割舌。斩首。”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烫进我的脑髓里。
挖眼。割舌。斩首。
不及格=挖眼+割舌+斩首。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感猛地冲上喉咙,我死死咬住牙关,才没当场吐出来。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四肢冰冷僵硬。荒谬,极致的荒谬感之后,是如同深海冰水般灭顶的恐惧。
“这……这是什么玩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微弱得如同蚊蚋,“谁搞的恶作剧?太他妈过分了!”
“不是玩笑,林默。”李明的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你生病的这三天……已经考过一场了。就在你回来之前……他们……他们真的……”
他的声音哽住了,巨大的恐惧让他几乎无法组织语言,他抬起颤抖的手,指向窗外。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挣扎着爬到床边,撩开那有些脏污的窗帘一角。
宿舍楼下的水泥空地上,空无一人。
但靠近围墙的那片原本长着杂草的泥土地上,有几块颜色异常深暗的区域,形状不规则,在灰暗的天光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黑色的、干涸的褐红。旁边,似乎还散落着几小团看不清具体是什么的、颜色同样深暗的东西。
没有尸体,没有残骸,只有那些刺目的、无声诉说着什么的污迹。
以及空气里,若有若无地,透过窗户缝隙钻进来的一丝……甜腥铁锈气,混合着消毒水也盖不住的,浓烈的血腥味。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
不是玩笑。
那张准考证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飘落在床单上,那行血红色的字依旧狰狞。
“他们……真的做了……”李明把脸埋进枕头里,压抑的、小动物般的呜咽从他喉咙里漏出来,“王涛……张健……他们都没及格……我亲眼……亲眼看到他们被拖出去……就在楼下……”
王涛,张健。班里另外两个成绩吊车尾的男生。平时虽然调皮捣蛋,但……
挖眼。割舌。
我感觉自己的眼眶和舌头开始不受控制地发酸,发痛,仿佛那想象中的酷刑已经降临。
“学校疯了?!没人管吗?报警!对,报警!”我猛地去摸枕头底下,手机不见了。我又翻身去翻床头柜,里面空空如也。
“没用的……”李明抬起头,满脸是泪水和绝望,“电话打不出去,所有人的手机……那天考试前就被收走了。学校大门……从你生病第二天就彻底锁死了,有……有人守着。”
我僵在原地,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
“老师呢?校长呢?他们就看着?!”
“老师……”李明的瞳孔猛地收缩,恐惧达到了顶点,“老师他们……都变了!”
变了?
就在这时——
“吱呀”一声。
宿舍门被毫无征兆地推开了。
一个身影站在门口,不高,甚至有些矮胖,穿着那件我们看了快一个学期的、深蓝色的旧夹克。
是班主任,赵老师。
他站在哪里,目光平静地扫过宿舍。
我和李明瞬间噤声,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连呼吸都屏住。我下意识地将那张飘落的准考证飞快地塞进被子里。
赵老师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往常看到我们时的恨铁不成钢,也没有任何异样的凶狠。他只是那么看着我们,目光甚至称得上……平和。
但我的心脏却在这一刻疯狂地跳动起来,几乎要撞破胸腔。
他的眼睛。
赵老师那双平时总是带着点疲惫,偶尔会因为我们考得实在太烂而冒出火气的眼睛,此刻,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均匀的、毫无杂质的……血红色。
不是布满血丝的那种红,而是整个虹膜,连同眼白的一部分,都弥漫着那种粘稠的、不祥的暗红。像两潭凝固的血液,深不见底,没有任何人类该有的情绪折射。
他就用那双血红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们,像是在确认什么。
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漫长如一个世纪。
几秒钟后,他什么也没说,缓缓地,几乎是无声地,带上了宿舍门。
“咔哒。”
门锁合上的轻响,在死寂的宿舍里,不啻于一声惊雷。
我瘫软在床铺上,冷汗瞬间湿透了单薄的睡衣,粘腻地贴在皮肤上。李明在旁边剧烈地颤抖着,牙齿格格打战。
那双血红色的眼睛……那不是人的眼睛!
那不是赵老师!
“看……看到了吧……”李明带着哭腔,“所有的老师……都变成那样了……红色的眼睛……他们现在是……是‘监视者’……”
监视者……
我猛地想起梦中那无法捕捉的沉重恐慌,此刻终于找到了源头。那不是梦!或者不完全是!那是我在高烧混沌中,身体本能感知到的外界剧变!
这个学校,在我生病的这三天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封闭的、按照某种恐怖规则运行的屠宰场!而我们这些“差生”,就是待宰的羔羊!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恐惧。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尽管四肢还在发软。我深吸一口气,再次爬到窗边,这次,我的目标是看向校门的方向。
宿舍楼的视角有限,但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两扇巨大的、平日里敞开的铸铁校门,此刻紧紧闭合着,上面缠绕着小孩手臂粗细的崭新铁链,和一把看起来沉重无比的黑色巨锁。门房的屋顶上,似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伫立着,穿着像是保安的制服,但姿态僵硬,同样拥有一双……在晦暗光线下微微反着红光的眼睛。
封锁。彻底的封锁。
我们被关在了这里。和一群眼睛血红、执行着“净化”规则的“老师”在一起。
下一次“特殊考试”是什么时候?准考证上没有写日期。但按照李明的说法,上一场刚结束不久,那么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我必须知道更多。
我缩回身子,压低声音,几乎是在用气流询问李明:“到底怎么回事?这三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一点细节都不要漏!”
李明蜷缩着,断断续续地,开始讲述那噩梦般的三天。
学校在我生病后第二天突然宣布戒严,所有通讯中断。然后就是“新规”颁布,措辞和准考证上一样冰冷。接着是强制性的“特殊考试”,题目难到离谱,监考的就是那些眼睛变红的老师。考试结束后,当场阅卷,当场宣布“不合格”名单。然后……就是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执行“第一阶段净化”。
“他们……他们力气好大,王涛想跑,被赵老师……就是刚才那个,一把就按住了,像按一只小鸡……然后……然后就用……用那种东西……”李明说不下去了,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学生呢?其他学生就看着?没人反抗?”
“刚开始有……几个高年级的想冲出去,被……被打断了腿,拖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后来就没人敢了……而且……”他抬起头,眼中充满了更深的迷茫和恐惧,“有些成绩好的……他们好像……没那么害怕……甚至……有点……”
他没说下去,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似乎出现了一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变化,仿佛这套血腥的规则,与他们无关,甚至……他们可能是安全的?
优等生……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火石般闪过我的脑海。
伪装!
我们必须伪装成优等生!
在这个疯狂的地方,成绩是唯一的生死线。至少在下次考试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表现得像那些“安全”的优等生一样。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不能引起那些“监视者”的怀疑。
同时……我们必须找出真相。学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老师们的眼睛为什么变红?这套“净化”规则到底是谁制定的?目的何在?只有找到根源,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我把我的想法飞快地告诉了李明。他先是茫然,随后眼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之火,但很快又被恐惧覆盖。
“可是……怎么装?我们的成绩……”
“不知道,但必须试试!”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晃了晃,试图让他振作一点,“听着,李明,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热爱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模仿陈涛,模仿李静!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陈涛和李静是我们班常年霸占前两名的学霸。
就在这时,走廊外传来了脚步声,不止一个。还有那种……冰冷的,金属物体拖曳在地面上的声音,令人牙酸。
我和李明瞬间僵住,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极致的恐惧。
脚步声在我们宿舍门口停顿了一下。
那一刻,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冲上头顶的声音。
然后,脚步声继续向前,渐渐远去。
我们瘫软在地,大口喘着气,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
不能等了。
我掀开被子,忍着身体的虚弱和无处不在的酸痛,开始换下睡衣。动作尽可能轻,不发出一点声音。
“你……你要干什么?”李明惊恐地看着我。
“去找线索,”我压低声音,语气是自己都意外的冷静,“不能待在宿舍里等死。我们必须知道更多。”
“可是外面……”
“外面更危险,但待在原地就是等死!”我打断他,套上校服外套,“你留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病还没好利索,在睡觉。我很快回来。”
我必须出去。我必须亲眼看看,这个学校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必须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或者……同类。
我轻轻拧开门把手,闪身出了宿舍。
走廊里空无一人,光线昏暗,两侧的宿舍门都紧闭着,听不到任何往常的喧闹声,死寂得可怕。只有头顶那盏接触不良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忽明忽灭,将我的影子在墙壁上拉长、扭曲、又缩短。
空气中,那股血腥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怪异气味,更加浓烈了。
我贴着墙根,像一只幽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
每一步,都踩在未知的恐惧上。
我知道,从踏出宿舍门的这一刻起,我的逃亡,或者说,我们的求生,已经开始了。
在这个眼睛血红的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