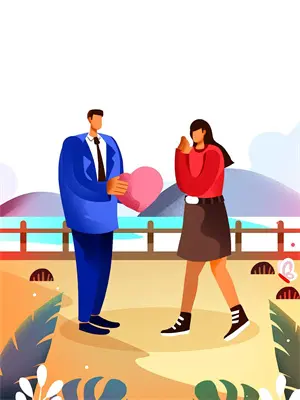
初夏的风总带着栀子花的甜香,傍晚的霞光把滨江路染成蜜色时,我第一次遇见宛若。
她穿着酒红色吊带裙站在江边护栏旁,裙摆被风掀起个好看的弧度,
手里把玩着一台银灰色单反,
指尖的碎钻美甲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那光芒像极了我后来无数个夜晚里,
想起她时心头跳动的星火。江面上偶尔掠过几只白鹭,翅膀剪开金色的波光,
她忽然举起相机,手腕轻转,快门声在风里轻得像一声叹息,我却听得格外清晰,
仿佛那声音直接落在了心尖上。我攥着刚打印好的简历,汗湿的纸角在掌心揉出褶皱,
边缘的油墨晕开,把“设计系毕业生”几个字浸得模糊。作为刚毕业的设计系学生,
连续半个月的面试失败快把我那点可怜的自信碾成了粉末。前一天在一家广告公司,
面试官盯着我的作品集冷笑:“连光影关系都搞不懂,还敢说自己学设计的?
”他指尖划过我画的海报,指甲在纸上留下一道白痕,“你这画的不是产品,
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色块。”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让我连抬头看路人的勇气都快没了。
可那天,我鬼使神差地停了脚步,看着宛若举起相机对准江面,
发尾的大波浪随着动作轻轻晃动,每一下都晃得我心跳漏了半拍。她站在霞光里,
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而我,只是个站在画外的、狼狈的看客。“你拍的话,
这里要低角度一点。”她突然转头,眼尾上挑的丹凤眼带着笑意,声音像冰镇汽水一样清爽,
瞬间浇灭了我心里的焦躁。我慌忙低下头,耳尖发烫,
能清晰地感觉到血液在耳朵里“嗡嗡”流动。听见她走近的脚步声,
踩着高跟鞋的声音在石板路上清脆作响,接着相机的重量落在我手里,
带着她掌心残留的温度,还有一丝淡淡的栀子花香——和晚风里的味道一样。“试试?
把晚霞和江面的倒影框在一起,这样能让画面有层次感。”她站在我身边,
肩膀离我只有一拳的距离,我甚至能看见她睫毛上沾着的细小绒毛,被夕阳染成了金色。
我僵硬地举起相机,手臂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
取景框里的世界突然变了模样:橘红色的云层层层叠叠,像被打翻的调色盘,
深的地方像醇厚的红酒,浅的地方像融化的橘子糖;江面泛着碎金似的光,
每一道波纹都在闪烁,像是撒了一把星星;而她站在镜头边缘,半边侧脸被霞光描上金边,
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按下快门的瞬间,“咔嚓”一声轻响,
我听见自己加速的心跳,比相机快门声还要响亮,震得耳膜发疼,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你看,是不是比平视拍好看多了?”她凑过来,肩膀轻轻挨着我的胳膊,
指尖点在相机屏幕上,“这里的倒影和晚霞呼应,画面一下子就立体了。你的构图很有天赋,
就是没找对角度。”她的头发扫过我的脸颊,带着洗发水的清香,
混合着她身上的栀子花香水味,让我紧张得连呼吸都放轻了,只能胡乱点头。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光圈快门聊到毕业规划,她是自由摄影师,刚结束一组婚纱外景拍摄,
背包里还装着没卸的镜头,
镜头盖边缘沾着一点婚纱的白色蕾丝线头;而我笨拙地说着自己对设计的想法,
连说话都不敢看她的眼睛,生怕她发现我眼底的窘迫——我连自己专业的“光影”都搞不懂,
又怎么敢和她聊摄影?分别时她笑着说:“你很有天赋,要是喜欢摄影,
下次可以一起出来拍。”她还留了我的微信,备注是“有天赋的小设计师”,
头像是一只举着相机的卡通兔子,可爱得和她性感的模样有些反差。
我把那张晚霞照片洗出来,贴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照片里的晚霞比我记忆中还要美,
而宛若的侧脸,更是被定格成了永恒的温柔。从此每天下班后,我就泡在摄影论坛里,
看教程、学参数,手机里存满了摄影技巧笔记,
夹:“风光摄影参数”“人像构图技巧”“后期修图步骤”……为了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
我戒掉了奶茶和外卖,每天中午啃馒头配咸菜,馒头是从家里带的,放凉了硬得硌牙,
咸菜是母亲腌的,咸得能噎住;周末还去兼职发传单,在商场门口站八个小时,
手里的传单被风吹得乱飞,有时还会遇到不耐烦的路人,把传单扔在地上,
我还要弯腰捡起来,拍掉上面的灰尘继续发。攒了三个月,
终于在二手市场淘到一台八成新的单反,机身有些划痕,镜头边缘也有轻微的磨损,
但卖家说“成像没问题,只是外观旧了点”。拿到相机那天,我抱着它在出租屋里转了三圈,
把相机贴在胸口,能感觉到机身的冰凉,还有自己滚烫的心跳。我兴奋得一夜没睡,
对着天花板练习举相机的姿势,直到手臂发酸。周末我跟着摄影社群去扫街,
社群里的人大多是有经验的摄影师,手里拿着的都是最新款的相机,只有我,
背着那台旧单反,像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刚开始拍的照片要么虚焦要么构图混乱:拍街角的老槐树,把树干拍歪了,
树叶还糊成了一片;拍卖早点的阿姨,把人家的脸拍得模糊,
却把旁边的电线杆拍得格外清晰。社群里的前辈老李笑着说:“小常,你这拍的不是照片,
是抽象画啊。”他接过我的相机,翻看着里面的照片,眉头皱了起来,“你看这张,
快门速度太慢了,所以虚焦;还有这张,构图太满了,没有留白,看着压抑。”我红着脸,
把老李说的每一个问题都记在本子上,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那天回家后,
我把每张失败的照片都导进电脑,用红色的笔在屏幕上标上问题,
然后对着教程一张一张地改:虚焦的照片,我就反复练习调整快门速度,
对着家里的盆栽拍了几十张,直到每张都清晰;构图乱的照片,
我就用硬纸板做了个简易的取景框,每天对着窗外练习构图,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手指磨出了茧子,握相机的地方,皮肤变得粗糙,甚至有一次因为握得太用力,
指关节都泛了青。存储卡里存满了练习照,从拍糊的街景到能抓住路人笑容的瞬间,
我终于慢慢找到了感觉——有一次拍一个小女孩追着蝴蝶跑,我蹲在地上,调整好快门速度,
在她张开双臂的瞬间按下快门,照片里的小女孩笑得灿烂,蝴蝶停在她的指尖,
阳光落在她的头发上,像镀了一层金边。老李看到这张照片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常,
有进步!这张有灵气。”再次约宛若拍照是一个月后,我提前一周查好天气预报,
确认那天是晴天,还特意查了薰衣草花田的花期,怕错过最佳拍摄时间。
我选了城郊的薰衣草花田,那里离市区很远,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再走半小时的路。
我还特意买了束向日葵,听说她喜欢这种热烈的花——前几天翻她的朋友圈,
看到她在一片向日葵花田里拍的照片,配文是“喜欢这种向着阳光的感觉”。见面时,
我手里攥着向日葵,手指都捏得发白,生怕花蔫了。宛若穿了白色连衣裙,
裙摆上绣着小雏菊,领口是浅V领,露出纤细的锁骨。她看到我手里的向日葵,
眼睛亮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向日葵?”我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看你朋友圈知道的。”她接过向日葵,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笑着说:“谢谢,很好闻。”在紫色花海里,她转圈时裙摆飞扬,像只蝴蝶,
阳光透过薰衣草的花瓣落在她身上,把她的白裙子染成了淡淡的紫色。我按下快门,
定格下她飞扬的裙摆和灿烂的笑容,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但这次,照片没有虚焦。
“进步好大!”她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眼睛亮晶晶的,像盛着星星,
“这张可以当我新作品的封面,比我自己拍的还好看。”她指着照片里的自己,
“你把光线抓得特别好,把薰衣草的紫色和我的白裙子衬得很和谐。”那天之后,
我们成了摄影搭档。她带着我去各种好看的拍摄地,春天去郊外拍油菜花,
那里的油菜花一望无际,金黄色的花海延伸到天边,她穿着黄色的连衣裙,站在花海里,
像一朵盛开的油菜花;夏天去海边拍日落,傍晚的海边,天空是渐变的粉色和橙色,
她光着脚踩在沙滩上,海水漫过她的脚踝,她举起手,
像是要去抓天上的云彩;秋天去山林拍枫叶,红色的枫叶落了一地,她穿着红色的风衣,
蹲在地上捡枫叶,头发被风吹起,落在枫叶上;冬天去滑雪场拍雪景,她穿着白色的滑雪服,
戴着红色的围巾,从雪坡上滑下来,笑容比雪景还要耀眼。她教我怎么找光线、摆姿势,
怎么根据不同场景调整参数:拍油菜花时,她让我用侧光,
这样能突出花瓣的层次感;拍海边日落时,她让我用大光圈,把背景虚化,
突出人物;拍枫叶时,她让我用逆光,让枫叶的轮廓发光;拍雪景时,她让我增加曝光补偿,
避免雪景拍得灰暗。而我把她拍进无数张照片里,她性感火辣的模样,
在镜头下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穿着黑色皮衣骑摩托时,她戴着黑色的头盔,
只露出一双眼睛,酷飒得让人移不开眼,摩托车的引擎声轰鸣,她转头对我笑,
嘴角带着一丝桀骜;穿礼服参加晚宴时,她穿着黑色的晚礼服,裙摆拖在地上,
戴着珍珠项链,优雅得像古堡里的公主,她端着酒杯,在灯光下和别人交谈,
一举一动都透着高贵;就连在家煮咖啡时,她卷起袖子露出纤细的手腕,手指握着咖啡壶,
蒸汽在她身边缭绕,都带着别样的魅力。我越来越心动,可骨子里的胆怯让我不敢表白,
只能把爱意藏在每一张照片里——我会特意选她最好看的角度,会把她的笑容修得更灿烂,
会在照片背后写下“今天的宛若,比阳光还耀眼”这样的话,却从来不敢让她看见。
为了靠近她,我开始学习后期修图,下载了各种修图软件,每天熬夜看修图教程,
眼睛熬得通红。我把她的照片修得更精致:调整肤色,让她的皮肤看起来更细腻;优化光影,
让照片更有层次感;甚至会在照片里加一点小细节,比如在她的头发上P上几片飘落的花瓣,
在她的身后P上一道淡淡的彩虹。我还亲手做了一本相册,封面是用硬纸板做的,
上面贴了几片干花——是上次去薰衣草花田时摘的,我把它们夹在书里压干了。
相册里贴满了我为她拍的照片,每一张下面都写着拍摄时的心情:“今天和宛若去拍油菜花,
她笑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花海都亮了”“今天拍日落,海水溅到了她的裙子上,
她没生气,还笑着说‘这样更有生活气息’”“今天她教我拍逆光,她站在光里,
我觉得她像个发光的天使”。她生日那天,我包下了一家小型摄影展厅,展厅不大,
只有几十平米,但我提前一周就去布置了:墙上挂满了她的照片,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拍的晚霞照,到后来一起去各个地方拍的照片;地上摆着几盆向日葵,
是我特意买的;角落里放着一台投影仪,循环播放着我为她拍的视频,视频里有她的笑容,
有她教我拍照的样子,还有我们一起玩耍的片段。我从傍晚等到深夜,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手里攥着准备好的告白信,信纸都被我攥得皱了起来。终于,她来了,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
看到展厅里的照片,她愣住了,眼睛慢慢红了。“常成,你怎么会做这些?
”她看着展厅里的照片,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眼里满是惊喜。我鼓起勇气,把告白信递给她,
结结巴巴地说:“宛若,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在江边给你拍照就喜欢了。
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好,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也没有多少钱,但我会努力,
以后我想一直给你拍照,把你所有好看的样子都记录下来。”她愣了愣,拆开告白信,
认真地看着,嘴角慢慢上扬。然后她笑着扑进我怀里,双臂环住我的腰,
声音闷闷的:“傻瓜,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说呢。”我抱着她,能感觉到她的心跳,
和我的心跳一样快。我抱着她在展厅里转圈,
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为我欢呼——墙上的照片在笑,地上的向日葵在笑,就连投影仪里的视频,
都在播放着她的笑容。那天晚上,我们在江边散步,她靠在我怀里,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我的脸上,有些痒。她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星光:“常成,
以后我们开一家摄影工作室吧,就叫‘光影约定’,好不好?我们一起拍很多很多照片,
一起把工作室做大。”我用力点头,把她抱得更紧,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实现这个梦想,
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开始一起规划工作室的事情,找场地、做预算、设计logo,
每天都过得充实又甜蜜。我们去看了很多写字楼,有的太贵,有的太小,有的位置不好。
终于,在一个老街区里,我们找到了一间合适的房子:一楼是门面,二楼可以住人,
租金不算太贵,而且周围有很多好看的老建筑,适合拍照。我们一起打扫房子,她擦窗户,
我拖地;她刷墙,我搬家具。墙面我们刷成了白色,地面铺了浅灰色的地板,
还在门口种了几盆栀子花——她说,等花开了,工作室里就会有好闻的味道。做预算时,
们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本子上:相机、电脑、打印机、装修费、租金……算下来需要不少钱,
我们把自己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不够的部分,又向朋友借了一些。设计logo时,
我画了很多草稿,有简约的相机图案,有光影交错的图案,还有我们两个人的剪影。最后,
我们选了一个由“光”和“影”两个字组成的logo,下面写着“光影约定”,
字体是温柔的曲线,像我们之间的约定。她接的单子越来越多,有时候要熬夜改方案,
我就陪着她,给她泡咖啡、煮夜宵。她喜欢喝不加糖的黑咖啡,我就每天早上早起,
给她磨咖啡豆;她喜欢吃我做的番茄炒蛋,我就经常做给她吃,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心里满是幸福。有一次我们去外地拍外景,住在山里的民宿,晚上突然停电了,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窗外的萤火虫在闪烁。我们点着蜡烛看照片,蜡烛的光在她脸上跳动,
把她的眼睛映得格外亮。她笑着说:“以后就算遇到再难的事,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怕。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我用力点头:“嗯,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可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矛盾就开始出现。
她的摄影事业越来越红火,接的单子级别越来越高,从普通的个人写真,到高端的婚纱摄影,
再到品牌的广告拍摄。客户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有的客户要求照片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拍,
有的客户要求照片的色调必须符合他们的品牌风格,
有的客户甚至会对照片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挑三拣四。而我还在起步阶段,虽然技术有了进步,
但和宛若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我常常跟不上她的节奏:她能在几分钟内确定拍摄方案,
而我还在犹豫构图;她能轻松应对客户的各种要求,
而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能在高强度的拍摄后,还精力充沛地改方案,
而我早就累得只想睡觉。有一次拍摄高端婚纱写真,客户是一对有钱的夫妇,
要求拍逆光剪影,背景是海边的日落。那天风很大,光线变化得很快,我没控制好曝光,
照片有些过暗,剪影的轮廓也不清晰。客户看了照片,
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专业水平?连个剪影都拍不好。
”宛若当场就发了脾气,当着客户的面说:“常成,你怎么回事?这么基础的问题都能出错?
我不是教过你怎么调整曝光吗?”我脸涨得通红,想解释“风太大,光线变得太快”,
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客户皱着眉头说:“你们这样的专业水平,
怎么敢接高端单子?我们的婚礼很重要,不能交给你们这样不专业的人。”说完,
客户转身就走,婚纱拖在沙滩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痕迹,像一道刺目的伤口,
划破了原本浪漫的日落氛围。我僵在原地,手里还握着相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海风卷起沙子,打在脚踝上,有些疼,却远不及心里的难受。宛若看着客户离开的方向,
胸口剧烈起伏,转身时,眼里满是失望:“常成,你知道这单有多重要吗?
这对夫妇身边有很多潜在客户,要是能做好,我们工作室的名气就能打开。可你呢?
连这么简单的逆光剪影都拍不好!”她的声音带着怒气,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我心上。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那天的风确实反常,光线变化速度远超平时练习的场景,
可看着她通红的眼眶,话又咽了回去。我知道,再完美的解释,也改变不了照片失败的事实。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们坐在车里,一路沉默。车载音响里放着舒缓的音乐,
却丝毫缓解不了压抑的气氛。宛若靠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眼神空洞,
我偷偷瞥了她好几眼,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从那以后,这样的争执越来越多。
有一次,我们接了一个服装品牌的广告拍摄,客户要求拍出“都市女性的独立与优雅”。
我熬夜做了拍摄方案,设计了几个在写字楼天台拍摄的场景,觉得能突出品牌调性。
可在团队会议上,宛若直接否定了我的方案:“常成,你这方案太保守了,没有新意。
现在的广告都追求视觉冲击,你这拍出来跟普通写真没区别。”我不服气,
辩解道:“可客户的品牌定位就是简约、优雅,太夸张的场景反而会偏离主题。
”“你懂什么?”宛若提高了声音,“我接过多少服装广告单子,
比你清楚客户真正想要什么。他们嘴上说要优雅,其实更想要能吸引眼球的照片,
能让消费者记住的照片!”会议不欢而散,其他团队成员看着我们,眼神里满是尴尬。
我拿着被否定的方案,回到座位上,心里又委屈又愤怒。我知道宛若有经验,
可她为什么就不能听听我的想法?为什么总是觉得我的方案不够好?那段时间,
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以前一起拍照时的欢声笑语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争执和冷战。我努力想跟上她的脚步,每天熬夜学新的拍摄技巧,
看最新的摄影杂志,研究热门的广告案例,甚至报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培训班,周末去上课。
有一次,为了学习一种新的光影拍摄手法,我在暗房里待了整整一天,反复调试灯光,
直到手指被药水染得发黄,才拍出一张满意的样片。我兴奋地拿着照片去找宛若,
想让她看看我的进步,可她只是扫了一眼,淡淡地说:“还行,但离专业水平还有差距。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所有的热情。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她正在和客户打电话,
语气热情又专业,挂了电话后,又马不停蹄地改方案,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失落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堵墙,我拼命想靠近她,可她却一直在往前走,
从来没有回头等过我。有一次我们因为工作室的发展方向争执,彻底爆发了。
宛若想扩大工作室规模,租更大的场地,招聘更多的摄影师和后期人员,接更多的单子,
尽快打响名气。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团队规模刚好,应该先把口碑做好,
保证每一张照片的质量,再慢慢扩大规模,一步一步来。“常成,你就是安于现状!
”宛若红着眼眶,声音带着哭腔,“我们当初说好要把工作室做大,
要成为行业里有名的摄影工作室,可你现在却只想守着这一小块地方,满足于接一些小单子!
”“我不是安于现状,我只是觉得应该稳一点,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工作室才能走得长远。
”我也红了眼,“难道规模大就一定好吗?要是我们把控不好质量,接再多单子,砸了口碑,
最后还不是一场空?”“我们看法不一样,没办法一起走下去了。”宛若的声音很轻,
却像一把刀,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坚持。分手那天也是傍晚,还是在初次相遇的江边,
同样的晚霞,同样的风,可身边的人却没了当初的温度。江水拍打着岸边的石头,
发出“哗哗”的声音,像是在为我们的感情送别。宛若递给我一本相册,
封面是我们一起设计的,上面印着“光影约定”的logo。我翻开相册,
里面是我第一次给她拍的那些照片,页面已经有些泛黄,每一张照片下面,
都有她用娟秀的字迹写的备注,比如“第一次和常成拍照,
他紧张得手都在抖”“薰衣草花田,他送了我向日葵,很开心”。“你很有才华,
只是我们不合适。”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
比如“我们再试试”,比如“我会努力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可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一句“再试试”就能解决的。
她转身离开,穿着我们第一次约会时的酒红色吊带裙,裙摆被风吹起,和初见时一样美,
可我的心,却再也没有当初的悸动,只剩下满心的疼痛。我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
直到消失在霞光里,手里的相册重得像块石头,眼泪砸在照片上,晕开了晚霞的颜色,
也晕开了我们曾经的回忆。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相机扔在角落落满灰尘,
工作室的规划图被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我辞掉了工作,每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像个行尸走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手机屏幕偶尔亮起,
却没有我想接的电话。母亲打电话来,听出我声音不对,着急地问我怎么了,











